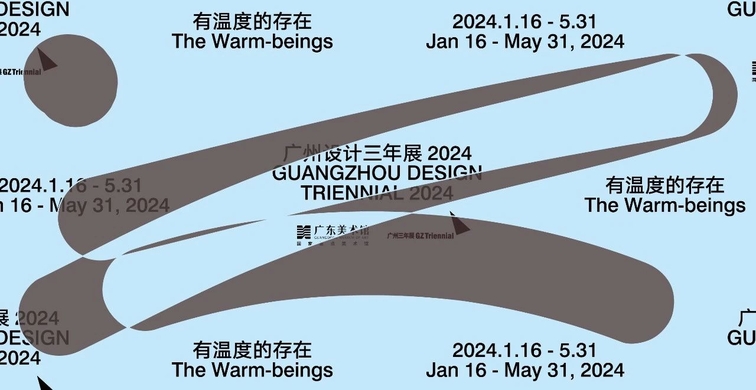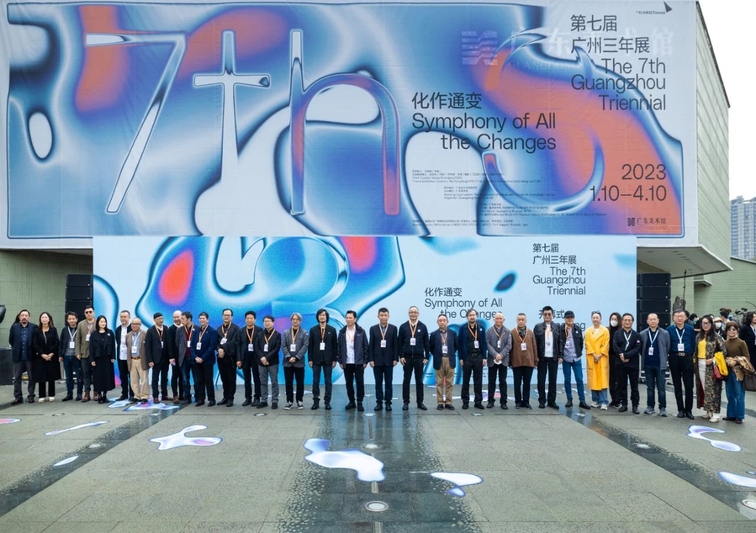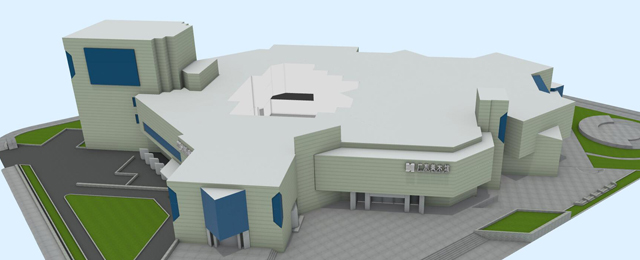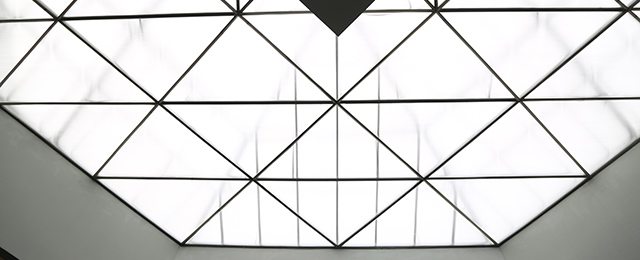玫瑰村的故事:司徒乔女儿司徒双讲述家庭老照片里的往事
录入时间: 2015-06-19
2014年7月5日,年届八十的司徒双老师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含泪画下去——司徒乔艺术世界的爱与恨》策展人曹庆晖副教授讲述家庭老照片里的往事。司徒双是画家司徒乔的二女儿,1995年退休前一直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拥有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真实的“玫瑰村”,是司徒乔与冯伊湄在法国相识、相爱的一处美丽的乡村。这里策展人取义象征,寓意幸福,意指司徒乔的家庭,这也是《含泪画下去》特设的一个版块。司徒双老师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就此话题在美术馆贵宾厅面对投影兴致盎然地侃侃而谈一个半小时,通过挑选的一部分家庭照片,别具风采地勾描出她的亲人所经历的国事、家事、艺事与诸多细节。当时列席者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副主任李尧辰、美术馆办公室杜隐珠、研究生宋金明和黄碧赫以及中央美术学院艺讯网摄像师胡志恒等。事后,先由宋金明具体负责对录音文字的处理和完善。之后,本着尊重讲述原意和集中讲述内容的原则,曹庆晖在参照冯伊湄《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8月北京第2版)的基础上,仔细校核时间与材料等细节,在对文字删繁就简后定名为《玫瑰村的故事:司徒乔女儿司徒双讲述家庭老照片里的往事》。文章完成后,曾交司徒双老师过目。
——曹庆晖2014年7月17日记

图1
司徒双 图1是我父亲司徒乔年轻时比较典型的一张照片,他在当时北京的燕京大学神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样子。我父亲报的是神学院啦,可其实真正并没有好好上什么课,而是画画去了。
曹庆晖 司徒乔留的八字胡,看着很讲究啊。
司徒双 我爸挺新潮的,属于那个时候的文艺青年。

图2
图2这张照片非常珍贵,是我父亲和岭南同学的合影,前排最左边是我父亲,后排中间最高的是冼星海。司徒乔和冼星海他们两个既是同乡,后来又是岭南同学,他们是发小、朋友,这个在我妈妈书里面有很多描述。冼星海旁边的女士,是我三姑姑司徒怀,弹钢琴的。家里说冼星海一直追求我三姑姑,有过这么一段,我三姑姑没有乐意,没有成,我家里人都这样说了。下面是二姑姑,坐在底下的这个。我父亲就这么两个妹妹。二姑姑后来嫁到加拿大去了。这些人差不多是出身岭南的文艺青年,爱国、热血,都有名字的,我现在说不全了。
曹庆晖 坐在前排右边的是二姑,后面怀抱左臂站立的是三姑,对吧?
司徒双 对。我爸爸在最左边,翘着二郎腿坐着的是我爸。冼星海个子很高,很帅的。

图3
图3这张也是司徒乔年轻的时候,也是20来岁,和他合影的这个人是一个很成熟的革命者,名叫张采真。他是党员、翻译家,是司徒乔的燕京同学,可惜1927年这个人被国民党杀了。我爸爸1927年曾经有一次短暂的武汉之行,就是张采真叫去的。也就是从张采真那里,最初了解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
曹庆晖 前面图2的照片里有没有这个人?
司徒双 没有,那拨儿是广东岭南的。张采真在党史里面有记载,后来牺牲了,这个照片非常难得。
曹庆晖 图3这张他们俩人的合影应是在照相馆里面拍的。
司徒双 嗯,很正式的感觉。
曹庆晖 不过,这个照片里您父亲的样子看起来比图1要稚嫩些。
司徒双 都是留着小胡子,是当时的时尚吧。
曹庆晖 相比起来,我觉得图1照片的时间可能还要靠后才对,它明显比图3要成熟。

图4
司徒双 图4是我母亲冯伊湄,这是她大学毕业的照片,她是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她不是上海人,是广东惠州人。我爸爸是广东开平人。他们是同省老乡。我的外公是一个大矿主,在江西开矿,很有钱,起初我妈妈是独生女,被送到上海学习,我妈妈14岁上诗词歌赋就样样都行的,这张照片是很典型的那个时候女学生的样子。
曹庆晖 也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民国文艺女青年的样子啊。
司徒双 图5这张照片太重要了。

图5
我父母的结合非常浪漫,因为他们出身太不一样了,可是居然就走到了一起,而且白头偕老,相濡以沫。我爸爸很穷,我的爷爷是个破产的小米店主,在乡间走投无路只能去闯世界,不知怎么歪打正着地进了岭南大学附小,管杂物,做的不错,后来学校让他搞伙食。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岭南大学附小是美国教会主办的,那是只有买办官僚子弟才念得起的学校啊,但它也有个好规定,就是校工可以免费送一个孩子上学。我爷爷有七个孩子,五男二女,我爸爸是长子,这个机会自然首先要给他嘛,所以我爸爸很年轻的时候英文就很流利。
我妈妈是一个大矿主的女儿,起初是独生女,后来有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弟弟,我爸曾画过他这个小姨子的肖像,这个像你在我们家是看到过的。我外婆是正室,只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妈妈,但这也就让外公有借口娶姨太太。我外公先后娶了七房姨太太,这七个姨太太只生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还不清楚是不是我外公真正的血脉,但名义上是这样的。
一个是富家大小姐,一个是穷小子,很不同的背景。但机缘巧合,他们1928年都到了法国。我爸爸去法国的船票和最初的费用是靠展览会和为旅馆画屏门嵌画筹措的。我妈妈则是坐着豪华邮轮去的,和她同船的乘客中有孙夫人宋庆龄。我妈妈曾经告诉我说,那艘邮轮上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不是水,是葡萄酒。这多少有点像电影Titanic那个意思了。我爸爸好像就是那个画画的穷小子,只不过我父母不是在海上同一条船上啊,他们是在法国本土相识的。
到法国以后,中国留学生圈子不大,大家有共同的朋友,这两个人很快就坠入爱河。一个穷画家和一个富家女恋爱,这个事情太浪漫了。但不久我妈妈那边出问题了。我外公经营的矿产被江西军阀夺了,很快就破产了,后来他因为做一小手术,在手术台上没下来。外公突然一死,七个姨太太就把东西都卷走了。我外婆急死了,叫我妈赶紧回来,还不敢说外公死了。这样,我妈因为接济断了,就从法国赶回来了。外公的七个姨太太把他剩下的那些财产都卷走了,只剩下两个小孩没有人要,扔给我外婆了,这样我妈妈就多了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喏,就是照片上这两个小孩子。我爸爸不久从国外回来,他和我妈妈不是在法国就好上了么,回来准备结婚,作为新女婿就得来见丈母娘了,所以就有一张很宝贵的合影。照片上我母亲的穿着,我外婆、我小姨阿琴的穿着,都还很讲究,虽然家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故。
我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从来没有嫌贫爱富,她嫁到司徒家没有享过一天福。我爸爸不到30岁就得了肺病,这个病在当时就像现在得了癌症一样伤脑筋,而且我爸爸是做的是最不赚钱的行当,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我妈妈结婚以后就得照顾一个生病的丈夫。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的经济来源主要出自我妈妈。她在外工作、教书,或者做文学编辑或者是做校长,家里都是靠我妈妈的工资生活,我爸爸拿不出啊,他就是想把艺术搞出来。我妈妈这样一个出身的女人,自己满肚子学问,却无怨无悔地支持她的丈夫做艺术。没有我妈妈,我爸爸早就没有了,也就不可能有我们姊妹们。我有时间真的要好好给我妈妈树一个传,现在人们知道司徒乔多一些,太少人知道他背后还有一个冯伊湄啊。
我妈妈出口成章能写诗的时候才14岁,她的理想就是当个作家,但是因为要负担家里啊,她没有时间投入。她有时间写书,是我父亲过世以后写我父亲的传记《未完成的画》,这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过。特别令人辛酸的是什么呢?我妈妈写的时候是1965年,当时广东美协的领导跟她说,你要好好把司徒乔的一生写出来,给她最好的条件,住在从化温泉,那是首长休假的地方,她什么都不用管,花一年的时间写出来了。但是,写出来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就别想出版了,还不够批判的呢。一直等到1976年6、7月份的时候,才第一次在香港出版。不过,我妈妈已经在1976年1月过世了,她自己没看到这本出版的书。
我妈妈真正做了一件好事!司徒乔的很多事谁知道呢?谁有第一手材料呢?不是我们这些子女,我们那时还小,有些事情不是我妈妈写下来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妈妈才是我父亲的知音,只有她知道我父亲怎样的劳苦,怎样不余遗力地追求他的艺术。我妈妈一辈子不管贫贱,不管什么情况,都永远支持我爸爸,都和我爸爸在一起。为什么我叫双,我妹妹叫羽呢?也就是因为他们俩情投意合的爱情。在南京的时候他们的朋友就把他们的住所叫“双羽楼”,就是两个人比翼双飞的意思,所以我叫司徒双,我妹妹叫司徒羽。有一个人给我写信,把“双”写成下霜的“霜”,有人给我妹妹写信,把“羽”写成下雨的“雨”,我们说这都成天气预报了,不是下霜就是下雨的,写信的人当然不知道这名字里面其实含有对我父母情投意合的赞美。
曹庆晖 您说的那本司徒乔传记的手稿捐给博物馆了吗?
司徒双 现在还在我们家,但那个不是我妈妈第一手的手稿,第一手的手稿有点零乱,后来司徒慧敏的女儿帮着抄了一遍,抄写的稿子在我们家。
曹庆晖 没有捐出去?
司徒双 我想以后是要捐的,后辈的人越来越不了解了,放在家里没有意义。
曹庆晖 您妈妈到法国留学,学什么专业呢?
司徒双 她其实去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估计是学文学,因为她一直学文学的。法国不是出了很多大文学家,大文豪啊,她向往那里,奔的应该是文学。
曹庆晖 她比司徒乔小几岁?
司徒双 小6岁,我爸爸是1902年,我妈妈是1908年,差6岁。

图6
图6很温馨,是我父母结婚后在广州生下他们第一个女儿。我妈妈抱的就是我姐姐,叫司徒圆。她脸是圆的,另外也是希望她一切都圆满。我姐姐现在已经过世了。

图7

图8
我是1935年生的,我妹妹是1936年生的,生我妹妹的时候我们家在南京。图7是我父母和姐姐还有他们的一位朋友在南京的照片。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我们一家都在南京,我特别记得家里曾经跟我讲,我们逃难先去了庐山。庐山植物园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正规的植物园,那个主任是植物学家陈封怀,陈封怀的父亲和我的外公是一起开矿的朋友,他们是世交,所以陈封怀马上打电报给我父亲,说你们赶快到庐山来,日本人一时半会儿到不了庐山,南京是首都太危险了。幸亏跑得快,很快南京沦陷,惨遭屠戮。但是日本侵略的脚步也很快,我们一家又匆匆从江西逃到湖北,在武汉曾经巧遇冼星海,在我妈妈的书里说冼星海曾经劝我父亲留下来投入抗战的洪流,可那个时候我父亲肺结核恶化,病的不轻,踌躇两天还是决定南下广东开平老家休养身体,到广州正好缅甸有华侨学校邀请我妈妈去教书,我妈妈希望我父亲能在一个远离战火的地方修养身体,于是,我们一家乘船去了缅甸。图8是我父母到了新加坡后的一张照片。
曹庆晖 我印象您父亲的年表里提到他是结婚第二年得的肺结核。
司徒双 在这个前后吧。他很年轻的时候得了肺结核,后来发展到三期,也就是这个病的最后一期。
曹庆晖 我很奇怪你父亲得了肺病为什么还老爱抽烟斗?
司徒双 艺术家就是这样的,要不他没有灵感。

图9

图10
图9是我们一家在马来亚。这段时间对我爸爸养身体有好处。珍珠港事变以前,东南亚没有战争,那边的生活很悠闲,也很好。
图10是也我们全家的合影。你看最右边那个女孩,也就是图5里我妈妈同父异母的那个妹妹阿琴,已经长成一个大姑娘了。那个时候新加坡和现在的马来西亚是一个地方,是英国的殖民地,并不分的。我们站在沙滩上,其实这个后面全是海,我们就在沙滩上的椰子林里面住,特别好。我已经有记忆了,我差不多5岁。我们早上一起来先到沙滩玩沙、游泳,然后再回来吃早饭,所以我现在还是特别喜欢游泳的。最左边的这个女孩是我爸爸这边亲戚的一个女儿,她的爸爸在那开椰子林。因为珍珠港事变,日本人进攻,天天空袭,新加坡这个地方根本不能挖防空洞,沙地上一挖就出水,只好跑到她家的椰子林躲躲。这是我们三姐妹,我是老二,前排右边的是姐姐,爸爸抱着的是小羽。
曹庆晖 这个阿琴姨后来去哪了?
司徒双 她后来就死在南洋了,她得了热病。她很漂亮,追求者排着队呢!

图11
图11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姨,右边第二个是我姨,最右边的是我姨的追求者,一个银行家,整天追着我姨。唉,可惜我姨死得太早了。热病很可怕,一下子高烧,人就过去了。

图12
图12就是我妈妈和我姨,她们感情很好的。

图13
图13我要说一下,这个是在马来西亚一个叫槟城的地方,我对这里印象特别深。你看我们住的像小木楼,在沙滩上面,那边就是海,你看楼底下都是虚的孔洞,不是实的墙。为什么呢?因为一涨潮海水把楼下淹了,这样就是准备让它淹的。我爸爸在这个地方弄一个秋千,我们在那荡秋千。我爸爸有一幅画叫《海滩上》,就是从我们窗户看出来的景。我爸爸在东南亚画了很多色彩非常绚丽的作品,他老说槟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云彩最漂亮的地方,因为热带的阳光特别足,很容易激发他的灵感。你看照片上我是不是一个乐天派?我是老二,最右边那个,总是笑咪咪的,最不安分的就是我,都说我是假小子,说我应该是男孩。

图14
图14是我和我姐姐在南洋的一张照片,我是不是像假小子?我像男孩,我特别淘气,敢上树,看见当地人爬椰子树,我也爬,上去一半就掉下来了,结果缝了好几针,我当时挺让父母操心的。

图15
图15是我的一张照片,说明那时候生活很安逸。我5岁生日时,二姑姑从加拿大多伦多给我寄了这么大一个娃娃,特别的高兴,所以照了一张。

图16

图17
图16和图17是我们三姐妹小时候在南洋一起玩的照片。右边是我,最不安分了,动来动去的,还在那说个不停。左边是我姐,中间是我妹妹。现在我姐姐已经走了,我妹妹脑溢血卧床,就我还活蹦乱跳的,但马上也80岁了。
曹庆晖 所以,如果没有抗战背景的话,单纯看这些照片,好像和战火烟云没有什么关系。
司徒双 珍珠港事件以前这里太平得很,而且生活节奏特别慢,人过得很滋润,太阳大的时候没有人干活,太阳下去的时候就唱歌跳舞,反正热带生活资源很丰富,容易生存,歌舞升平的。
曹庆晖 这些照片能留下来是家里面有一个相机吗?还是你父母的朋友给拍的?
司徒双 这个没有印象了。我们经过太多地方,国内国外跑来跑去的。我记忆里我的童年整个就是逃难,我从两岁开始逃到十几岁,1935年到1945年,我就记得我没有在一个学校待过六个月以上。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接触许多语言。我的语言好,能讲好几个国家的语言,而且我善于模仿,到一个地方就学,到四川学四川话,到广东学广东话,出国就学人家那里人讲话,有些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出生地,学外语就够呛。

图18
司徒双 图18就是我父亲在新加坡最重要的油画创作《放下你的鞭子》,具体的过程就不说了,我妈妈的书里有记载。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记忆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金山,那绝对是漂亮小生的样子,到我们家一化完妆就成一个老头了,而且往那一站眼泪立马流下来了,进入角色快啊。这一点我爸爸特别佩服,说这是真正的演员,要他演什么他马上成为那个人,很让人信服。所以我爸爸使劲画,这么大一张画我爸爸两个礼拜画成了。
曹庆晖 您知道您父亲和金山、王莹之间以前有来往吗?
司徒双 好像没有。新中国成立后,我父母从美国回来住在香山,我听我妈妈说起过王莹也住在香山。其实我想在1949年以前,他们应该是互相有所耳闻的,当然应该是我父母知道金山、王莹更多些,毕竟他们是名气很大的电影和话剧演员。

图19
图19前面中间是我妈妈和姐姐,她们后面是我爸,这应该是在马来亚的时候和他们交往的朋友的合影。在战争没有临近前,人们都是很安逸的样子,没有什么恐惧,什么不安都没有。
曹庆晖 你有没有听妈妈讲过,他们在南洋时有什么比较熟悉的画家和朋友?
司徒双 郁达夫在那,但好像也不是很熟。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姊妹都还小,虽然有些事有记忆,但还不大懂事的。
珍珠港事变后,南洋就开始炮火纷飞了,那一幕太惊险了。日本侵略者特别毒辣,他占领一个地方,先把这个地方那些有名的知识分子控制起来,要么就是砍头,因为他觉得你是有头脑的人。我爸爸在南洋已经有一些名气,所以必须走,不走就完了。后来流亡到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最终还不是被日本宪兵给杀害了么。我们一家好容易才坐船逃离新加坡,这个我妈妈在她的书里有一篇脱险记专门写过。我自己记得我们坐的船到马六甲海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当时有两条船,船上让乘客穿救生衣,我很雀跃,什么都不知道,到甲板上看到所有人都在祷告,我想游泳那么好的事为什么祷告,现在明白了,要是一个炸弹下来,谁救谁啊,那么大一个海。炸弹真的掉下来了,幸好没有掉在我们船上,但另外一个船中弹了。叶公超,后来去台湾做了外交部长,他的叔叔是民国时做了多年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叶公超是我爸爸的朋友,他在另外那艘船上,他后来让英国海军救生艇救上来了,救上来的是很少数的,反正我们是九死一生。
我们从马六甲海峡跑到缅甸,还没站住脚,日本鬼子就撵过来了。我们又接着从滇缅公路跑,滇缅公路处于原始森林里,那时公路还没修好,日本人知道那是唯一的交通线,整天在那轰炸,条件特别艰苦,这样跑了一年到了重庆,受了好些罪。

图20
图20这个太宝贵了,我那个时候已经记事了,这是团山堡,距离重庆七十里。我们从新加坡逃难回来,借这个地方作为临时居住的地方,算是暂时有一个安定的家。这里的茅草房,原本是漫画家高龙生搭建的。后来我到四川专门去找这个地方,房子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这个地方建了公路,全都没有了。隔着水那边有一个地主的大院,这个地主大院住着傅抱石一家,所以我们这两家非常近。傅家有几个儿子,我们家有几个闺女,那个时候双方父母还想给我们定娃娃亲呢。我跟傅小石、傅二石都是发小,很好的朋友,很多共同的记忆都在这里头。这个地方现在除了这张相片什么都没有了。

图21

图22
图21是我妈妈在团山堡的茅草房外的一张照片,房外自己搭一点架子,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因为起码没有日本人追了。
这种条件下我爸爸妈妈继续做一些创作,像图22这样,说明他们不管什么情况还是坚持做他们的东西。
曹庆晖 你妈妈的衣服是自己做的吗?又合身又合体的啊。
司徒双 我妈妈原本又不会做饭,又不会做针线,她是大小姐出身,小时候她有四个丫鬟服侍她。解放前好多人家因为灾变或者破产,几个铜板就可以买一个丫鬟,所以她有四个丫鬟。到司徒家她什么都干,而且她没有抱怨,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父母一个搞文学一个搞绘画,而且我妈妈永远是我爸爸作品的第一个观众。我爸爸的一篇日记说,只要看见我妈妈的一个微笑,他认为就不白费劲,得到肯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容忍的那种,而是互相了解和崇拜、信任的那种,这个真的很难得。

图23

图24
你看图23就是那茅草的房子,这是从里面往外打开窗子的。我对这个房子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是我爸爸在这里创作了《国殇图》。图24就是我爸爸在这张画前的留影,这个很了不起的,可惜原画已经没有了。这张画,你看看有多高,从房顶一直到下面。这张画表现的是为国捐躯的那些英烈,不分党派,只要是抗日的英雄,都有,有名有姓的。为什么要画这样的画呢?主要是我们从南洋逃难回来以后到了重庆,我爸对那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有触动。我们小孩印象最深的是,画这张画先摆一个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凳子,凳子上再弄一个小凳子,我爸爸得慢慢爬上去,我妈妈特别担心,因为他身体不好,肺病快到三期了,又没有营养,怕他累,也担心他不留神栽下来。但我爸爸说,画这些人应该跪着画,现在站着画还敢说累吗?我妈妈书里面对这个有记载,我爸爸是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来画的这件作品,但这张画现在没有了,非常可惜。我们小孩晚上不敢进去,因为画上画得都是死去的烈士,而且没有眼睛,眼睛这块是白的,原来这张画的名字就叫《死不瞑目》。我们小孩子不懂这些了,觉得害怕,晚上一定不去我爸的这间画室,这个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我爸爸有玩命的精神,他真正想画的时候,什么都不顾,我妈妈在那着急他也不管。

图25

图26
图25是我跟我妹妹坐在院子里面吃饭,狗还抢食呢。
图26是我爸爸从新疆回来后和我妈妈的合影。这张照片后面这个亭子叫“四空亭”,什么都没有,四面风都吹来,一个茅草的,我爸爸说就叫“四空亭”。我爸爸到新疆后,我们担心得要死,但是有一天突然看见一个维族大叔一样的人回家了,就是我爸爸。自从去了一次新疆,我爸爸就特别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维族人。他对新疆的土地和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感情。今年6月在新疆美术馆展出我爸爸当年在新疆的写生,一片好评,他们说新疆现代美术史,是从司徒乔开始的。你想想,1943年左右,有谁去画过新疆和那里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呢?我爸爸新疆写生有两百多幅,他的画是非常鲜活的民俗风情的反映,不带任何偏见,他自己也真是热爱新疆。
我爸爸当年去新疆跑了不少地方,后来有学者曾手绘过我爸爸走新疆的路线图。但是当时新疆的政治气候比较危险,军阀盛世才独裁统治,这个军阀什么人他都敢杀。我爸爸因为在新疆的活动也上了盛世才的黑名单,不过因为我爸爸是个画家,在新疆跟着骡车、马车到处跑,到处画,行踪不定,居无定所,一时半会儿真还不那么容易就找到他,所以我说是艺术救了他。

图27
图27我搞不太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看起来像是在大西北写生时留下的一张牧民和马的照片。我见过我爸爸有一个小的速写本,把马的每一个部位都做了详细的记录,马后头怎么样,前头怎么样,蹄怎么样,头怎么样,做了详细的研究。他敢画,他实在对那种很壮观的套马等大西北广漠天地独具的生活很感兴趣。这里我加一句,我爸爸1950年从美国治病回来后曾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想把鲁迅的全集都画上插图,他已经画了几个,第二是回新疆一趟,结果两个都没有实现,他走得太早了。

图28
1946年,我爸爸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聘请,赴粤、桂、湘、鄂、豫五省灾区考察,以画笔记录灾区情况,然后通过展览去募捐,把钱拿来救济难民。我爸爸得了这个任务后是非常兴奋的,他说这辈子就想画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所以这是他最愿意做的事。而我妈妈担心得要死,这个时候抗战刚刚胜利,满目疮痍,交通不行,供应什么都不行,而且我爸爸已经是三期肺病,怕他顶不住,车、船什么都没有,只能骑马。图28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就是我父母在灾区考察写生路上拍的骑马照。右边这位是我的一个表叔,他身强力壮,我妈把他找来陪他们一块,怕半路上有什么事,全都是骑马,所以很艰苦的。这个时期的写生也是我父母密切协作的时候,妈妈每天记日记,走到哪里了,画了什么,爸爸画上的词都是妈妈写的。

图29
图29也是很宝贵的一张,是我父亲面对《父女》这张画构小图。《父女》这张画是我爸爸灾区写生中的一张代表作。

图30
图30是我父亲拿着《义民图》竹笔长卷拍的照片,《义民图》也是灾情写生中的一件代表作。这里要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爸爸自己发明了竹笔,因为他觉得毛笔那个毛太软,于是他把头去掉,把竹竿削尖了以后蘸墨。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一方面保留了中国画笔墨的基本因素和特性,另外就是经过加工使得笔这个工具使用起来比较有劲道。他在美国时曾经发表了一篇《竹笔论》,我认为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快捷有力,对于丰富他的写生表现力非常有好处。

图31
图31是我们三姐妹在香港的时候。
曹庆晖 这个大概是四十年代末了吧?
司徒双 对。我父母是1946年去的美国,那个时候医生说我爸爸只有三个月的命了,因为只有美国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父母就把我们放到香港外婆家,我们在香港读书,四年没有见到父母。
曹庆晖 那个时候通信应该多。
司徒双 父母老不放心,总是写信,苦口婆心地说,我们有时候不爱看,我们这些小姑娘们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听话的。我们那时在香港受殖民地文化影响较多,很高兴看好莱坞电影什么的,我姐姐大一些,我记得我爸爸妈妈的信里就告诫过类似的问题,这些信我也要找一找。

图32
图32是我父母去美国治病前的全家合影。有我父母,我的外婆还在,我们三姐妹,还有我九舅公和九舅婆。九舅公是我外婆的第九个弟弟,为什么和他关系那么好呢?因为我妈妈年轻时到法国,一个大姑娘去海外读书不太让人放心,谁陪着呢?就是她小舅舅。我外婆是老大,这个九舅公是最小的一个弟弟,他的年龄和我妈妈差不多,他一直陪着我妈妈去法国,他在法国修的法学,回来是广东省法学院的院长,现在过世了。这是在香港照的,因为我们三个在外婆这儿,我父母坐船从那走。那个时候说心里话,我们小孩不知道着急,大人知道我爸爸凶多吉少,因为链霉素找不到或者链霉素不起作用的话他就死定了,所以可能是最后一张照片了,是这样的意思。

图33
图33是我父母在去美国的船上照的,我爸爸那个时候已经很瘦了,老爱戴一个维族的帽子。
曹庆晖 这个感觉不像在船上啊,会不会是从新疆回来后拍的照片?
司徒双 不是,我妈妈跟我说过,她说是在船上,赴美的照片。

图34
图34是到美国了,俭俊和我爸爸是同宗,我爸爸那个时候很瘦,这个照片是打链霉素之前。
曹庆晖 他怎么还离不开烟斗啊。

图35

图36
司徒双 图35也是刚到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当地华侨媒体给我爸爸做过一些宣传,图36就是。

图37
图37是我爸爸已经打了针以后的照片。我爸爸的这个病也挺怪,前后打了三个疗程一点效果都没有,都觉得不行了的时候,在第四个疗程奇迹出现了,好得也比较快了。
曹庆晖 不知道这个照片谁拍的,拍得挺好。
司徒双 这是在美国拍的,具体谁就不知道了。
曹庆晖 妈妈有没有说她会拍。

图38
司徒双 不会,我妈妈这个不行。她会写文章,诗词歌赋第一名,其他的不行。图38是我妈妈在纽约,那个时候才四十几岁。
曹庆晖 你妈妈在书里面描写他们在美国治病的时候生活非常煎熬。
司徒双 对,你看她这张照片好像很好的样子,其实她在美国一天打三份工。那时我们姊妹都在上学读书,父母要寄钱回来供我们读书,美元特别值钱啊,她打三份工才勉强够他们在美国生活的基本开支和我们姐妹三人的学费。我们之前不知道她那么辛苦,现在知道了,没有我这个妈妈,我们根本不能受良好的教育,但是她永远不会表现出来很狼狈啊,很忧郁啊,没有,这个很了不起的。

图39

图40

图41

图42

图43

图44

图45
图39-43大概是我父母在纽约第五街画室里的一组照片,其中记录下了我父亲为我母亲画像的片段。图44-45是我爸爸链霉素注射起作用了,身体和精神都有很大恢复,大胡子也剃了。
曹庆晖 这些照片都拍得真好,自然又很专业。
司徒双 那时有好多画家在纽约租画室,我父母也租了一个。他们当初是打算留下来的,因为我爸爸身体恢复的不错,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人也胖了不少,也可以画了,所以为他以后的发展做了铺垫。而且我妈妈在那时也得了一个聘约,就是VoiceofAmerica的中文编辑。VOA是全球广播最牛的了,有中文广播,我妈妈中文特别好,就特聘她做VOA的中文编辑。除了给高薪外,三个女儿到纽约的机票也全部给予报销,我们都在家里等着三张机票呢。但这时他们俩开始思想斗争了,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何去何从呢?当时有两大派,一派靠近台湾,一派靠近大陆,最后他们下了决心回国。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我现在能够体会,是从最苦的时候过来的,苦在没有自己的国家,中国人到处让人瞧不起,这种情况下你在国外是不可能心安理得的,这种民族自尊,这种感情胜过一切,比生活优越更重要。很多人反对他们回来,而且医生说我爸爸没有完全养好,很可能因为最后一个未愈合的空洞而致命,最后不幸被医生说准了。
我们有一个本家叔叔叫司徒展,是医生,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父母从美国回来到香港把我们全家带走,那个时候在罗湖交接,我们进关他们出关。司徒展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协和医院一人一栋小楼,生活很好,但他们很害怕共产党,那个时候他们全家都走了。我们因为是本家,在罗湖正好碰上,我们进,他们出,我特别记得那个叔叔说你们干嘛,跑回来干嘛,但实际上谁也没有办法让对方明白,你都得往自己的方向去!我后来在洛杉矶碰到司徒展叔叔,他比我爸爸还年长,保养得特别好,他一再跟我说,你们不应该回去,不回去现在跟我一样肯定特别好,我呵呵笑着,也不说什么了。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想得很辩证,假如从我父亲个人的身体讲,确实应该留在那,生活已经没有问题了,我妈妈一份工资就足够了。但是,从对民族的贡献和我父亲的心愿来讲,留在那他不会快活,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为这个国家出力。

图46
图46是我爸爸回国以后的照片,显得很健康,意气风发的。
新中国当时对归侨的接待规格是很高的,在香港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欢迎宴会。我们一家在香港接上外婆,在广州接上爷爷,三代人浩浩荡荡开向北京。我记的最清楚的是过武汉时还没有桥,是把火车车箱一节一节分开,船拉过去再接在一块,这样从广州到北京用了五天。
我父母到北京以后,我爸爸在香山弄了一个大宅子、大画室,高兴得不得了,他一辈子没有过那么大的画室,可香山是避暑的地方,那个房子墙缝那么大,冬天没法保暖的。第二是没有医生,交通不便,不像现在,当初他一出事什么都来不及。所以艺术家考虑问题总是从艺术想得多,但你起码要有点生活常识吧,你得保证自己活得下去啊,他可不管那么多,哇,太美了,太好了,这么大一个画室。他画的最后一幅是《秋园红柿图》,我们买的院子里有很多的柿子树,挂上柿子以后很美丽的。他画完就完了,他是春节前一天走了,太冷了,本来他身体抵抗力就差,然后生多少炉子都保不住温度。而且回国之后的营养条件也不行了,我一到香山就想起来我跟爸爸放羊,因为没有牛奶,他身体恢复又需要,就养羊喝羊奶。我们跟他放羊走到卧佛寺,不要钱的,现在到那里一看,什么过去的影子都没有了。

图47
图47挺宝贵的,司徒乔兄弟的合影。前面我们见过我二姑姑和三姑姑,这是他们兄弟的合影。司徒乔兄弟共五人,其中老四在加拿大,是一个人造钻石的工程师,做得很好,也是现在唯一在世的一个了,剩下的这四个都走了。我爸爸是老大,在右边。他左边第二个是老五,是在你们学校雕塑系教雕塑的教授司徒杰。左边第三个是司徒汉,是老六,他在上海特别有名。老辈的人一说司徒汉,都说他是群众歌咏运动的创始人,多少万人的大合唱都是他指挥的。我现在碰见的老人都说司徒汉指挥得特别好,《东方红》最初的时候是他们几个人搞的。他原本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不务正业”搞音乐,没有搞新闻。他很早参加革命,我们家到延安去最早的就是他。他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曾经被抓进监狱里面,监狱外面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开过追悼会,谁知他在监狱里还在指挥狱友唱《黄河大合唱》。以后他想法跑到延安去了,解放后就一直在上海,上海人对他比较了解,现在已经过世了。左边这个最小的叔叔最可怜,他跟着我奶奶,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炸死,造成他精神分裂,生活不能自理,糊里糊涂一辈子,也去世了。
在我们广东开平,司徒是一个很大的姓,出了不少人,我们司徒家这一代有三杰,就是司徒乔,司徒杰,司徒汉,一个绘画,一个是雕塑,一个音乐,都做出过一些成绩。
这是1950年左右拍的。当时我爸爸从国外回来,司徒汉常常来北京开会,司徒杰就在美院,要不是这样这哥四个也凑不齐。

图48

图49
图48-49是我们在北海的全家福,那时我上高中,我姐姐上大学,我妹妹上初中。
曹庆晖 最右边是你。
司徒双 对,左边是我妹妹,前排中间是我姐姐,我外婆是在北京去世的。这张照片和我父母俩人的那张合影,是同一天在北海公园照的。
曹庆晖 姐妹三个人后来学什么,做什么,父母有什么干预吗?
司徒双 没有,我们家特别民主。我姐姐特别喜欢文学,我妈妈培养的,但后来也没有继承,她上了北师大,原来她英文很好,后来又学俄文。我上了北外。我妹妹一直喜欢音乐,我妹妹有画画的天分,我记得她小的时候照着镜子画自画像,我爸爸很惊讶的。但是我爸爸的政策是谁也不许画画,因为他一辈子太苦了,所以不许,所以我们别的都可以学,就是不学画了,最后我妹妹是在星海音乐学院教钢琴了。

图50
图50也是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姐妹三个都成年了,这个好像是景山公园。

图51
图51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胸前还戴着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徽。

图52
图52是我爸爸走了以后,我们家就剩女将了,我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女儿的一张草地合影。其实当年在逃出新加坡以前,我妈妈就怀孕了,到重庆团山堡以后曾经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对这个弟弟有印象,我们姐妹老去抱他,但是这个小弟弟在九个月时夭折了,因为战争期间没有奶粉,我妈妈也没有奶,光靠那些杂粮糊糊是养不活的。小弟弟的夭折让我父母难过的要命,因为总还是喜欢有个男孩子,来了一个却没有养活下来。

图53
图53是1958年我爸爸去世的葬礼。你看见司徒杰没有,靠门站着,旁边这个是司徒杰的夫人,我的五婶,她现在洛杉矶,91岁了。

图54
图54是廖承志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廖承志是我爸岭南大学的前后同学,对我爸爸有了解,也比较敬重,所以当年出版画册的时候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还有廖承志本人,都曾经写过序言。

图55
图55是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一次遗作展览,是1962年在王府井老美院的陈列馆举办的。那个地方特别好,虽然小了一点,有很多人踊跃来参观。我觉得梳两个大辫子的那个背影就是我。
曹庆晖 日常在家,您父母相互之间怎么称呼?
司徒双 她叫他乔,他叫她伊湄。
广东美术馆
2015年6月18日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冬日的寒凉抵不过大家的热情。 广东美术馆的这个冬天, 因为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