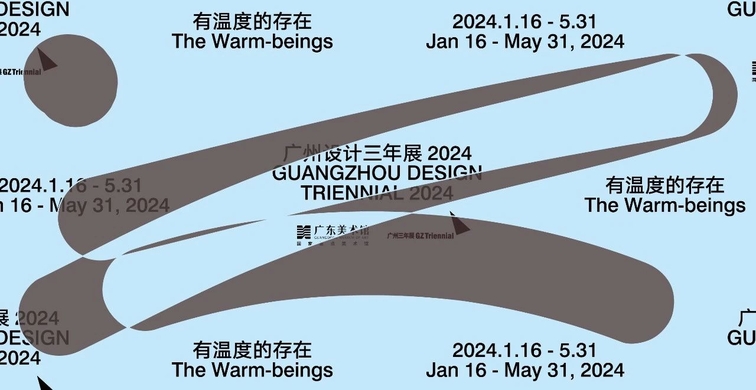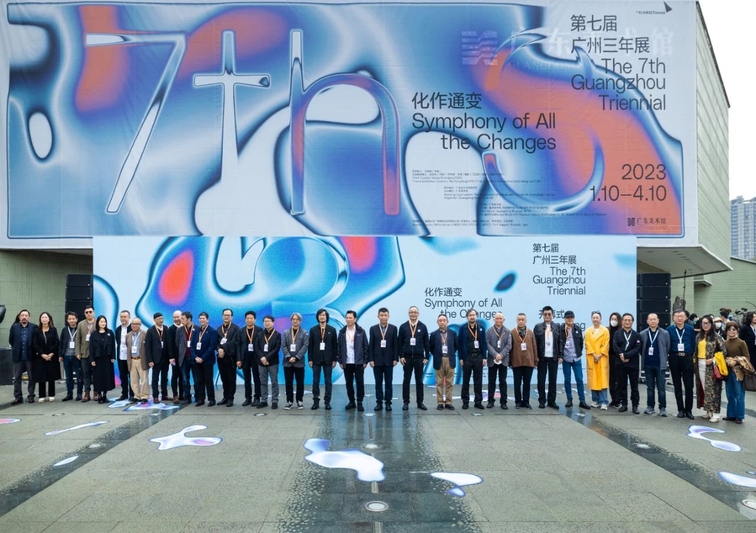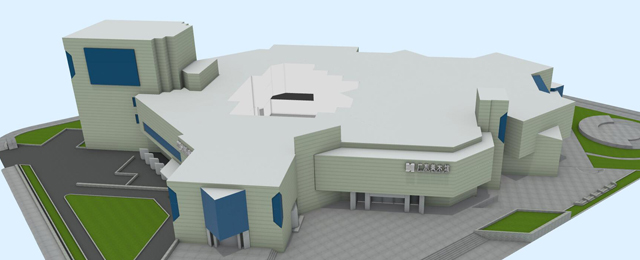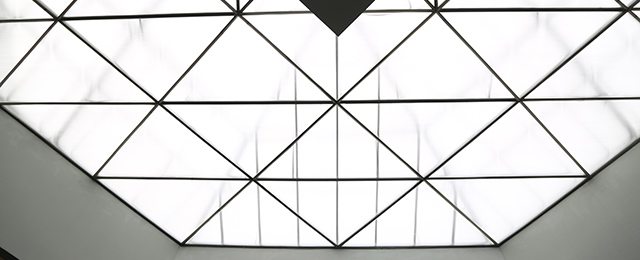都市流行色——读刘斯奋人物画新作
录入时间: 2014-06-19
陈迹
近十余年来,刘斯奋的现代文人画颇是引起美术界的关注。
这种关注既缘于刘氏在从政、文学、绘画、诗词、书法、学术等多个领域的自如穿梭及各自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更缘于其在从古装题材人物画向现代都市人物画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其他画家难以企及的综合素养和历史洞见。最近两三年来,刘氏更以纯水墨的具有白描意味的传统文人画笔墨技法,逐渐从对带有历史沉积感的都市俚俗风情的关注,转向对消费主义影响之下现代“都市流行色”更为明确的文化审视。这种转变,既令到刘氏现代文人画的价值指向进一步明确,也使他笔下的现代都市人物形象更为独特而鲜明,这体现了刘氏艺术思想和艺术手法在近年的进一步成熟,同时,也为传统文人画的当代介入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正如美术史教科书所描述的,人物画是中国画各门类中发端最早的画种。然而,由于这一画种从一开始时的“功利”属性,因此,自唐末五代文人画逐渐兴起之后,其中心地位便渐渐为山水画所取代(花鸟画也在这一时期日见兴旺)。至明代董其昌时候,“南北宗说”在绘画领域的正式提出以及董氏对南宗绘画不遗余力的推崇,文人画的正宗地位更在理论层面上得以确立,并几成一统中国画坛之势;而这种借物写心,“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水墨画形式,通常又以山水、花卉等为表现题材,即使是人物画,也大多以佛、道、高士、仙人、仕女之类的形象出现而殊少描绘现实的生活场景;在笔墨技法和作品图式上,也往往程式化为一种无论是画者抑或是观者都“约定俗成”的风格模式。这种现象无疑进一步加速了人物画日趋式微的颓势,并一直持续至上个世纪之初始渐有改观,而这一改变最为直接的作用力则是西方画学对中国绘画传统的巨大冲击。正因为西方画学包括人体解剖学、透视学等在人物画创作上的积极意义极为明显,其所带来的对传统绘画精神的消解也更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这,是我们所尤需警惕的。
美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经这样强调:“不要去发现什么,而是要去拾取我们丢失的东西。”是的,从“五四”以来的新美术思潮——尤其是1949年以后奠基于素描造型训练与写生实践的所谓学院派人物画风格以行政的方式在全国各美术院校的强制性推广,使到传统文人画中极受重视的笔墨精神受到普遍的弃置,而由此造成的中国人物画在“民族性格”方面的缺失无疑也是明显和令人遗憾的。也就是说,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救亡图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由于过分地强调美术的现实功用因素,而使到许多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的优秀绘画传统有被扯断的可能性,而其中尤以人物画为突出。另一方面,传统绘画中人物画的相对薄弱,又为这一画科在具有西方画学背景的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可能性。因此,刘斯奋在这个时候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有别于其他画家的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借鉴传统文人画的艺术手法来切入对现代都市生活情景的表达,无疑具有强烈的文化针对性和美术史意识。这种选择,一方面显然是基于刘氏对自身长短的清醒认识和判断,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基于其对历史文化潮流的敏感和对中西绘画历史的洞达。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对刘氏介入现代都市生活表达所采用的看似“保守”的“文人画形式”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虽然,“以古为新”是中西文化史上共同的重要演进脉络,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又如中国的魏晋玄学、唐代古文运动、清代碑学等等,然而在艺术自律的形而上信念普遍缺失,而民族文化的未来利益又往往屈从于现实需求和即时效应的当下,刘氏的这种选择既要在拒绝社会化的孤高寡合状态中剔除信而好古的迂儒气,同时又要通过跨越古人的已有成就而成就自我,这无疑需要深邃的历史洞见和卓越的胆识。
究实,艺术创作是极其感性的个人化情感活动,画笔一碰于纸,所谓的理论即形同虚设。然而,理论性的推设和价值判断有时又或可有助于美术家更为明晰自己的艺术道路。具体到刘斯奋的“都市流行色”系列创作,他在以文人画笔墨模式介入现代都市生活表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独特的介入视角,无疑应该引起美术界对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反思。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刘氏的文人画创作模式因其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之下有着过于强烈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而难以具有普适的意义。也就是说,刘氏所选择的,是一条无论在创作的主体、或者在创作主体的文化知识结构等“硬件”的要求上,都会对大多数当代中国画家“拒之门外”,而对刘氏本人来说则又是极其理想的个人化的艺术之路。
“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这是陈衡恪在其《文人画之价值》中对传统文人画的概述。
“文人”之谓,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是有特指的,并非认识几个字能吟诵几篇歪诗、或者又如现代的知识分子便可以称之为“文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和选官制度是紧紧地拴在一起的。“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译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因此,传统的“文人画”也称为“士夫画”,是官僚士大夫们案牍之余或诗文之余的一种消谴形式——这或可视为官僚士大夫画家们对他们所身处其间的社会现实的一种精神平衡和逃避。基于此,在传统文人画中,我们难以见到“现实社会”的种种世态,这是传统文人画的特点,也为文人画当代介入和发展的可能性埋下了伏笔。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文人画的创作主体——“文人”的征选机制从此中断,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各级官僚阶层中更鲜有能称之为“文人”者,更遑论像刘斯奋这样在文学、绘画、学术、诗词、书法等多个相关领域均取得甚高成就的具有真正传统意义的文人。这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现实,而这种现实也注定了刘氏这一创作模式的难以普及性。
另一方面,在新中国学院式美术人才培养机制之下,即以“非官僚”身份而在创作上具有文人画风格的专业画家来说,由于大多数并不具备文人画所要求的综合文化素养,因此,即使他们的作品在技术或图式上表现出所谓的文人画风格倾向,但往往因缺乏全面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的深度而停留在对传统笔墨图式的玩弄上,而在人文精神层面则缺乏深度的观照。1980年代后期兴起的所谓“新文人画”,虽然在抵制其之前几十年的政治对艺术的钳制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立场和超越功利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传统意义文人画所要求的创作主体的缺失(新文人画群体中并无一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支撑着传统文人画审美价值理想的农业文明社会在中国的逐步为工业文明社会所取代、以及这一画家群体普遍守成传统文人画笔墨图式的“小家寡人”般的墨戏心态,都无一例外地限制了他们作品的深度,并成为他们以文人画艺术方式切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障碍。
以上的喋喋不休,并非要证明文人画风格的中国画在当下的尤应重视和惟一正确方向,也并非要证明刘斯奋现代文人画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因为对“血统论”的过度强调,只会使我们将非“传统”的人类其它文明成果拒之门外!然而,在现实的当下,如何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获得一个当代的延续,无疑是每一位中国画作者所难以绕开的问题,而刘斯奋借鉴传统文人画的艺术手法来切入对商业社会潮流影响之下都市生活表达的角度和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水到渠成的妙得。
现代大都市的形成是建立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而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流行”的特性,“流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通过商业目的的策划而绞起的大众群体消费行为。这种由商业目的绞起的生活潮流,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敏锐的艺术家也必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此有所反应;同时,这些变化也必然会触动艺术家从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从全国各地的中国人物画创作状况来看,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表达,为近年来创作一大转向,而尤以中青年画家的都市介入为多。总的来说,这类都市题材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多借鉴西方的画学因素,这一趋向一方面是由于几十年以来美术院校教育模式的影响和1980年代以后西方美术思潮在中国的大量涌入;另一更为内在的原因,则是由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艺术与同样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现代都市文化之间的天然亲和力。这类作品普遍存在强调娱乐性或人性欲望、紧张、焦虑等倾向,而在人文关怀方面,则普遍缺乏更深层面的触及;另外,这种创作倾向对中国画文化属性的持续消解也是明显存在的。总的来说,商业文化正在以各种错综复杂的表现方式改变着左右着生活在其中的艺术家们审视社会现实的立场和角度。刘斯奋的“都市流行色”系列现代文人画,虽然也对消费时代都市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予以真切的关注,所描写的也是喧嚣都市的生活场景,但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平和而舒畅,而用笔甚至比他颇为成熟的古装题材人物更是简洁肯定,用墨也素净清朗;在画面的结构方面,则融入了某些适合现代都市表达和现代审美感受的构成元素以及现代水墨画的某些因素。观刘氏的“都市流行色”,并没有这一题材作品普遍存在的心神不定的躁急、狂怪、荒诞,而是一种容与的雅正、一种融融的春意,并有一股浓浓的文学意味融于其间。毫无疑问,刘氏独具文化个性的都市生活表达方式及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意味,与其身为现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特定的地位境遇,都有莫大的关系。作为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刘斯奋的现代文人画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旁观者”的超脱心态;作为一位现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刘斯奋的现代人物画又有深入生活现实的强烈的人文关照和社会担当;作为广东画院的院长和专业画家,他在“公余”或“诗文之余”的创作心态之外,又多了一层从“专业”上来审视自己创作的自觉——具体到技术层面,“都市流行色”系列作品中时代女性准确而又凝练传神的人物造型,毫无疑问有来自西方人体解剖学方面知识的影响,然而其“造型”所用的简括、俊朗、洁净而又富有节奏美的线条,既与其颇具成就的书法在笔调上保持相当的一致性,又可从苏仁山、丰子恺等前代画家的人物画作品中窥见其笔墨风格的传统画学资源。显然,无论从笔墨图式的风格倾向还是作品的文化意蕴和价值指向等方面来考察,刘氏独具特色的“都市流行色”系列现代文人画创作,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特殊的文化意义。
刘斯奋曾经说过,“在写作界的眼里,我是从政的(或者还是画画的);在绘画届的眼里,我也是从政的(或者还是写作的);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我又是写作和画画的。这情形,十足就像老故事当中那只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刘氏这一段自嘲式比喻文字,刊于《蝙蝠的意象》颇为显眼的扉页和封底。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得出,刘氏对于自己的“蝙蝠”身份,在“自嘲”之外其实更富有自信的意味——他自号“蝠堂”可为此说佐证。是的,作为一位画家,只有建立在对自己有着深刻认识的自信之上,才有可能在群星灿烂的历史长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氏能够以其对中国人物画历史的洞见,深刻而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人物画在当代发展的可能性和历史与现实留给当代人所能拓展的空间,以及自己的“蝙蝠”身份对传统文人画中的人物画科进行现代拓展的可能性和难以取代性。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刘氏深邃的思想穿透力和“不安份”的艺术性格,在不久的将来,他的艺术世界定会有另一番的壮阔和精彩。
在小文结束之前,笔者想补充强调,影响现代中国画走向最为直接和持久的,莫过于社会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和美学理想对中国画创作带来的改变,由是观之,中国绘画史上历时最为久远、而影响也最为深广的对文人画的推崇,其实质也是一种由文人士大夫所主导的艺术思潮。然而,在当代的中国,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文人画”已经失去其普遍存在的生长土壤,因此,刘斯奋在现代文人画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其意义并非在于其为人们提供了某种创作的范式,而更在于刘氏的绘画思想以及其对绘画个人化的理性介入角度和方式,给予“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的众多画者的警醒。
2007年7月14日于留留书屋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冬日的寒凉抵不过大家的热情。 广东美术馆的这个冬天, 因为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