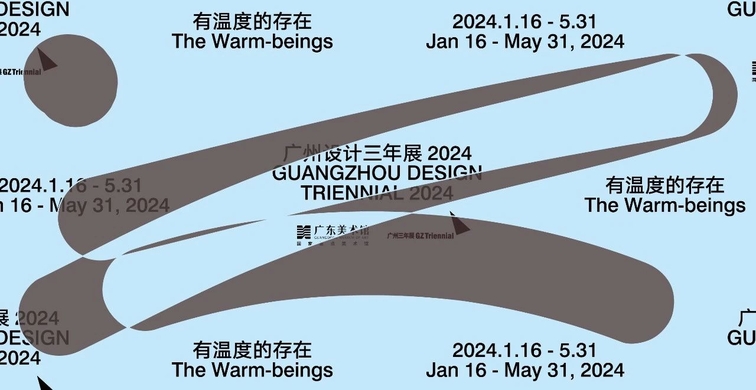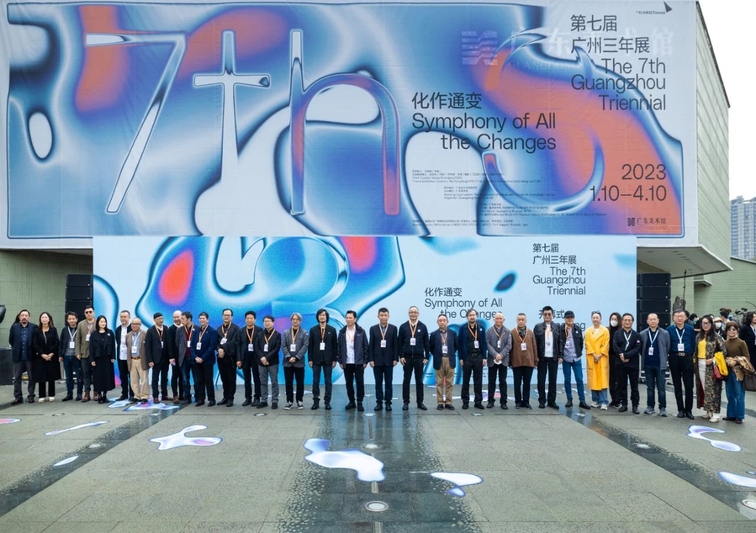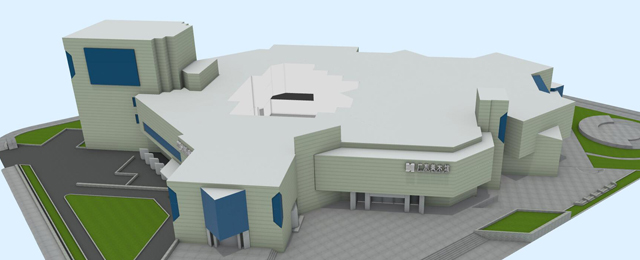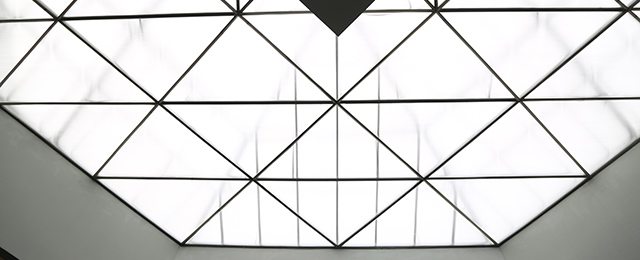石鲁的旅程与艺术风神石鲁论纲二题(刘曦林)
录入时间: 2007-08-21
石鲁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他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建设时期踏入画坛。民族危亡之际,他是一位以美术为武器的青年战士;50、60年代,他是探索中国画新徒的最具创造性的代表之一;在“文化大革命”那非常的岁月里,他是最敢于抗争的杰出的艺术家。他的人生旅程即艺术旅程。
石鲁始终是一位参与型的艺术家,而且将他的全部聪明才华,以强烈的艺术风骨和鲜明的个性意识奉献于他崇仰的理想,成为当代中国画史上突前的闯将。但他的旅程过度的坎坷,却类如历史上的屈原、司马迁、鲁迅这类人物的命运。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忠贞,始终伴随着对他的误会、压抑甚而摧残,而正是这种压抑和抗争的矛盾冲突益发显示出他英雄主义的本色,益发显示出仿佛有预见似的思想的真理和艺术上的超前意识。
一、人生与艺术的旅程
1.“冯门九子”--古文化与民族艺术启蒙
“冯门九子”是石鲁后期经常画在字画上的“印章”之一,意在表示自己的身世--本名冯亚珩,在同辈中排行第九。也许,他注定就是现代一大批曾被贬为“老九”的知识分子们的命运--挣脱封建家庭的羁绊,奔向自由和理想的归宿。经受超常的考验,做出超常的奉献,又免不了“文革”的灭顶之灾;待迎来了新时期的曙光,却抱恨未实现艺术的最后升华而长眠九泉。
据石鲁生前回忆,冯氏家族祖籍江西景德镇,其高祖避税迁四川,贩药售棉赢巨利,并于仁寿县文公镇安家,其后成为仁寿县第一大粮户,又按照《红楼梦》大观园的格局修建了冯家庄园。他在这个家庭了得到过物质的享受,亦受到封建家规的桎梏,看到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败落和分化,也在这个颇有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受到了从《三字经》到《说文》、《诗经》、《古文观止》和唐诗第一等系列古文化的教育,受到了喜藏古董字画和吟诗作赋的家风的熏陶,特别是从事美术的二哥冯建吴的深刻影响。但是他不能忍受直接施行封建家教的母亲的威焰和高压,也丝毫没有继承祖产成家立业的兴趣,少年时代就出奇的“捣蛋”,甚至于往他讨厌的私塾先生的茶壶里倒尿,因乳名是永康就被人骂为“糠谷子”、“糠猴子”。他聪敏、好强、孤傲而不复管教,并于15岁时离家,奔向他二哥执教的东方美专的校园。这是“冯门九子”对封建家教的第一次叛逆,是依着个性和兴趣的第一次自我选择,并预示了他人格成长和艺术风神的未来趋势。
东方美专2年的学习时间,他在家庭经济封锁的困境中,学习了中国画、西洋画和图案画的基本知识,全身心地投入了艺术。在他二哥的教导下,他懂得了书画是崇高的事,尤拜赏石涛、八大山人等文人作家的反抗精神和悲壮的审美内涵,自谓“颇受为艺术而艺术的清高思想影响”①。他曾到峨眉山旅行写生,并将中西绘画技巧相结合,自创一新格调。这位孤高学子投学不为谋职,当美专改为职业学校时离去,回乡担任了小学教员,并在抗日宣传活动中萌生了献身民族斗争的宏愿。
封建礼教再度向石鲁袭来,他不满于12岁时母亲就为他包办的婚事,母亲逼婚甚紧,无奈婚后三天即离家出走,奔华西协和大学读社会科学,不久又退学驰陕西抗日前线,其中从四川绵竹到陕西宁羌(今陕西宁强)是骑脚踏车完成了他人生转折点上的重要里程。
20岁的石鲁彻底德摆脱了家庭的羁绊,“冯门九子”终成“冯门逆子”。他早年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古文化和传统中国画的思维,他只是初步地接触了西画,而且从一开始接触,就萌生了沟通中西艺术的创造意识,使其文化和艺术的启蒙又汇入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潮流,并成为他中、后期艺术的重要铺垫。
2.延安赤子--作革命的艺术家
由天府之国转向黄土高原,是石鲁人生和艺术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他此前接受的中国传统文人画抒发情志的艺术观,以及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论,而在延安则逐渐转变为为人民大众而艺术,在当年即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革命的完全新型的艺术观。自到达延安,他改名为石鲁,以表示对石涛和鲁迅的崇拜,也表现出他欲将艺术的创造和革命的理想统一为一体的愿望,按照他个人当时的说法,“我的路子就是作革命的艺术家”。
延安10年,石鲁主要是普及革命美术的一位革命青年美术工作者,并坚持从事速写练习和连环画、插图、版画创作、40年代后期,渐次形成了以线刻为主兼及阴阳体面的木刻风格。如果说他有些超常的话,那就是在格外强调政治的氛围里,他自觉地意识到了强调艺术性的必要,即便是拉洋片也要拉出一个新名堂出来,在那些土戏台子上也要创造性地从事舞台美术设计。他善于作理论的高谈阔论,被普遍认为“高傲”和“个性强”,时与上级发生不同意见的冲突,拒不接受不正确的批评的犟劲,以及他多次检讨的“个人英雄主义”,实际上,倒是处处显示出以为找到了理想归宿的青年,那种永无休止的进取精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显示出他在共同的事业里高度尊重个性的胆识,这已经预示出一位大师应有的气质。
延安,使他的世界观和人生安排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这黄土高原上感到舒畅,并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也在这里获得了爱情的自由,甚至不顾同仁的反对,与性子泼辣的漂亮演员闵力生结成了终身伴侣。他在这里呼吸到远比冯家大院自由的空气,但冯家大院这家庭出身也给他带来过不少误会、挫折。他没有走回头路,把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了。他在这里顽强的寻找着集体与个人意志的统一,理想与自由的统一,和这片黄土地上的人民、风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奠定了人生和艺术的出发点,奠定了生活和情感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黄土地,就没有石鲁,就没有这位南方人的北方画,就没有日后流贯在他艺术中的坚定的艺术观念与信天游般的自由相共生的高亢的腔。
3.长安巨擘--当代中国画的一曲高腔
进入50年代,一直到“文革”之前,石鲁从而立之年步入不惑之年。在这段社会相对稳定,在中国当代史上称作“17”年的时期,他开始恢复因战争中断了10年的中国画的创作,从美术普及转向艺术的提高。在整个中国画坛经历的“改造”旧国画的思潮里,在50年代再度发生的中国画的论争中,这位善于从宏观上把握方向、道路的艺术家,明确地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试图在历史的文脉与现代的空间之间架起一座可行的桥梁。他通过对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的再度研究,批驳了“中国画不科学”的论点,认定了民族艺术的综合性特征,形而上的美学品格,孜孜于研究规律和方法,努力创立自己的新的艺术形式;他认定了生活、大自然这个艺术之源为“第一需要”,与西安的一批同仁坚持在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寻求创作的灵感,他比那些被称为“传统派”的画家更尊重传统的真髓,但他对传统的、世俗的似乎是超前的大幅度变革又为传统派所不容,被认为是“野、怪、乱、黑”的旁门左道,在和平时期,他又经历了艺术思想上的一场“战争”。
“17年”中,石鲁的特殊贡献一方面是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变化,从自然到艺术的升华中,他由倾向于生活的叙述和大自然的客观事实,逐渐向突出主观情感和宏观的表现侧倾,从工谨的或者小写意的手法比较快地跨向纵笔写意的阶段,并且以《转战陕北》等一批精品为标志,形成了人物、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五十年代末到60年代初,俨然以戛戛独造的面目和磅礴的气势向中国画坛劈面而来,把整个现代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创作观念引领到一个新的层次。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位学术带头人,同赵望云等一批长安画家,在黄土高原上扬起了一股强筋的“西北风”,呼出了北国的雄强气势,可谓是当代中国画的一曲高腔。他们的作品通过1961年的“西安美协国画研究是习作展”震动了北京和全国画坛,际被誉为“长安画派”,与傅抱石为核心的“江苏派”(又称“新金陵画派”)携手称雄于当代中国画史,从而改变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地域性画派的重心。而石鲁就是长安画派的理论中坚和艺术巨擘。
同一时期,石鲁对艺术的认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并撰《学画录》等几部手稿,在一系列艺术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视为“继古开今,创作批判”的纲领;提出了“生活决定精神”而“主体为人”、“物化为我,我化为笔墨”的主、客观关系;提出了“以神造形”、“画贵全神”的新的形神观;提出了笔墨为“主、客观交织之生命线”、“思想为笔墨之灵魂”、“意、理、法、趣求笔墨的笔墨”……这些观点,洋溢着创作精神和辩证思维,并以主体意识的强化成为其理论体系的特征。这些理论和其作品相互映照,成为石鲁趋于成熟的标志。
4.“芦屋斗士”--抗争意识与“反叛”艺术
“文革”之前的1964年,政治上的重压和严重的肝病已同时向石鲁袭来。但病中的石鲁并未能幸免“文革”的横扫。他曾两度从囚禁的“牛棚”中外逃,被逼食生包谷还未忘记留下一个日后还报的借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石鲁,在自称为“芦屋”的斗室里,奇迹般的创作一大批诗、书、画、印,表示他的愤慨和抗争,奇迹般的迎来了他的第二艺术高峰,但也因此成为“批黑画”风潮中的典型,被批判为“野、怪、乱、黑”派的代表人物,“文艺黑线回溯的急先锋”。彼时,他身着肥大过膝的长衣,须发上翘一如其硬骨头精神。在那个一切被颠倒的年代里,他的生活也整个被颠倒,像叫化子一样浪迹市井,或嬉笑怒骂无常,或自弹自唱自语,以至以酒代饭,如疯如痴如醉。精神分裂的病症并没有模糊他的信念,在重大问题上却与越来越加清醒。他曾表示“要把我的艺术思想改变,不可能!如其那样,不如罢笔。”1975年赠友人的书法作品,就超前地书写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正因为如此,他成了“新帐旧账一起算的人物”,身心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摧残。
历史的进程表明,他是一位从不苟且偷生的为真理而战的勇士,这个疯人是那个发疯的时代里最正常的一位艺术家。而历史的一度逆转几乎杀了石鲁,却未能改变他的志向,而只是过早地结束了前一段写意艺术的日程,并使后期艺术发生了特异的变化,即向着高度雄强和狂放期的变化。笔墨的恣肆狂放,线条的金石气的外现,思维的神秘怪诞,使其后期艺术成为高度表现型、倾泻型的艺术,思想内面的鲜明指向和艺术形式的强悍表现,构成了那特殊时代里的“反叛”艺术,也是最具有真理光芒和阳刚正气的艺术。
“文革”结束后,石鲁有过短暂的春天,不幸的事却在病床上度过。他曾经表示:“不必要肠断,还要留下肠子工作”。但终因晚期胃癌而过早辞世。
石鲁没有走完他理想的旅程,在艺术上也有诸多未了心愿。但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与艺术的旅程上,体现了人生与艺术的深刻联系。从“冯门逆子”到“延安赤子”的转化,从“长安巨擘”到“芦屋斗士”的转折,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文化背景决定了的一种变化。从古文化到现代文化,从倾向于表现生活的描写到主、客观的融合,并在这种融合中强化主观表现,也是中国现代大文化背景下艺术的趋势。石鲁在其人生与旅途上,对旧时代的叛逆,对新时代的顺应,在特殊时代里的反叛,始终证明他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和思想史上的强者。
二、 石鲁的艺术风神
石鲁是个大才,全才。在当代艺坛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具有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在诗、书、画、印的综合成就上达到如此高度,于绘画这一部分又同时在人物、山水、花鸟这几大部类取得全面的突破;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思想的深度和形式的张力上达到自成体系的谐和,在人格与艺术风神的统一上有那样强悍的独立表现。
1. 艺术风神的变化和人格的高扬
石鲁赞同“风格是人”的论断。但其早期,他的英雄主义气质更多地表现为对待事业、对待艺术从不满足的一种精神。在50年代前期的作品中,考虑生活的生动性、形体的真实感的因素偏多,技法上尚不熟练,笔墨的表现力也较弱,还没有形成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起码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随着方法问题的解决,主观意识的增强,那种宏观的、崇高的美学品格,男子汉的气概,才通过壮伟的结构和造型,浑朴的、大刀阔斧的笔墨和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一种以雄阔为主要特征的艺术风神的产生,标志着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石鲁的个性的确立。他在这第一高峰期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确切地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是社会共同理想的个性化表现,在当时却被批判为“野、怪、乱、黑”,这种文化现象本身,只是说明了保守主义的短视,证实了石鲁艺术的超前表现。石鲁1963年的在笔记本上回答“野、怪、乱、黑”的韵文,与其说是反驳,倒不如说是犹感不足的表示,那种“我更野”、“不为乱”、“不太黑”的态度,愈加显示了他“不屑为奴偏自裁”的治学品格,也说明了石鲁还不满意于自己的艺术,尚未达到他心目中理想的“搜尽平凡创奇迹”、“无法之法法更严”“黑到惊心动魄”的境界。“文革”中称石鲁十二句诗为“反动艺术纲领”,他反而进一步“野、怪、乱、黑”,也进一步地明朗了他的艺术个性。
“文革”中,即石鲁后期或第二高峰期的艺术表现,是整个中国文艺界“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的正常艺术思维的中断。他那种孤胆英雄式的反抗,不仅是捍卫真理、真知的信念,也使他高洁纯贞的人格得到高扬,是“风格与人”的更高境界的统一。他当时曾言:“艺术家的原则不需用策略来保护、艺术家只靠真善美。”虽慨叹“一代书生太笨,不懂天地风云”,却一如既往地斗争,正如其子石果认为属于“乐观主义的反叛型”,这种毫不妥协的硬骨头精神,坚持真善美反对伪艺术的明确思路,表现艺术风神上,是思想的真理性,情感的爆发性,笔墨的倾泻性,以及与这种精神相一致的阳刚之美,金石力度,半空杀纸的气势,不羁的野性的流溢,不避霸悍的锋芒,可以说是真率的狂放,是一个更真实的石鲁的表现。如果说这是一任主观的“自我表现”,在这“自我”的背后,是所有为坚持真善美而斗争的正直的人们的群体的呐喊,在这主观之中,包含这历史车轮不容倒退的客观真理。石鲁后期的艺术内涵和艺术风神,不是用一般的文人画作或男子气、大丈夫气可以涵盖的深刻性即在于此。
以上石鲁艺术风神的纵向变化的略述,只是其风格流向的主脉,随着境遇和情绪以及艺术对象的变化,又表象出含蓄、深邃、神秘、明艳、秀雅等多种支脉的风神和技巧、手法的多样性变化。但雄阔阳刚的风神,作为其风神的泉脉,是石鲁之所以是石鲁之所在,其丰富的表现是石鲁作为完整的、复杂的、多侧面的石鲁之所在。
2.“主体为人”--天人合一论的现代表现
中国古代艺术受哲学之影响,在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上,以相互依存、共生共灭之和谐为出发点,主张天、地、人的统一,或曰天人合一。石鲁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他的艺术中体现着这些宏观意识,并以强调人在自然,宇宙中的主观能动性为特征,形成了新的主、客观的统一,新的天人合一观。他认为“物为画之本,我为画之神”,“生活之主体为人”,从而赋予天、人关系以现代化内涵,并在其人物、山水画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就其人物画而言,人的主体地位有一逐渐升华,逐渐强化的过程。《古长城外》、《工地之夜》等50年代的作品,在天人关系上有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哲学倾向的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其《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东渡》等史诗般的代表作中,往往将人的形象融入自然之中,将人与自然融铸为一个整体的、富有意味的造型,通过整体的天人合一的博大感,强化主题,强化人的精神力量。整体性地处理即是精神性的、魂魄性的处理。这不仅是同时长于人物、山水画的石鲁的构图方式,更是他整体地观照人在自然、宇宙历史中的价值的思维方式。它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情节式绘画”的构思方式,但其精神性的容量却超过事件的再现性方式。它不同于人隐逸于自然、超然于尘世的古代的天人合一关系;而强化了人作为世界的主宰,人可以能动地借助于自然把握自己、把握历史命运的时代意识。这和石鲁一贯操守的世界观、理想信念取得了内在的一致。这可以说是“以神造形”论较之“以形写神”论在主、客观的比重上的差异给予现代人物画的变革,从哲学上说,也可以说是以主题为人的思想给予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表现。而且这种现代表现,是现代社会的历史的情思,与现代的造型方式、现代的中国画语言结合为一体的整体表现。
石鲁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天人合一观,在其纯粹或基本上以人为形象的作品中,有着类似的表现。《归宁》中的少妇内心的喜悦与翔飞的喜鹊情绪上的共鸣,《快活神仙》、《抽烟的老头》中那种农家场院里的人生情趣,是热爱人生,多情善感的石鲁的精神的另一个侧面。而《插麦人》,《船夫习作》和《高原人的脊背》这类作品,陕北汉子裸露的背部所呈现的力的美,是石鲁的代表性的人格和美学品格的体现。这些作品很少或完全没有自然景色的陪衬,但人的这种壮美的精神性品格,所有赖以共生的自然环境、历史风云,是可以通过画外之画的想象来实现的自然、历史与人的统一。
“文革”期间,石鲁通过加工50年代印度、埃及写生人物而产生的那批特殊的、充满着神秘的纹锦、符号、文字、画印的“怪画”,尽管那些题字和印文至今还不得通释,但从意境和可识的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得出他对抗“文革”的主题。可以领略到他对于被神化了的“狗类之宗法政权”的憎恨(《印度少女》),对于被蛛网围困的纯洁人格的赞美(《阿拉伯少女》),对于能“劫后复生”、“伏虎降龙”的神力的希冀(《印度神王》)。尤其在1970年完全新画的《美典神》中,从精密的线描所塑的神的气质与大片血红色的构成,从“没有天良就是丑恶”、“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等题记中,透析出他在逆境里对假恶丑的鞭笞,对真、善、美的向往。在这些病态中不失理性,神秘中精神明确,可以使人联想到天上与人间、历史与现实的属于别格的作品里,不仅提供了中国画的现代形态的一种样式,而映照着对于真善美的魂魄式的追求意念。这也许也意味着更趋向于人的主观世界的现代意识,对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的革命性的改造,对现实与浪漫相结合的以人为主体的思维方式的拓展--拓展为宇宙、灵魂、拓展为永恒的美的价值的宏观思维。
3.山水即人--现代山水画观念的变革
石鲁作为一位山水画家,其早期峨嵋写生到底如何有所创意已无从查考,其后山水画的进程大体与人物画同步,即从参用西法写生到以无法写意,从尊重客观的写实到物我交融的意境的创造,最后到人格化的表现的过程,从笔墨较为细弱到雄阔浑重,最后至劲峭雄放的变化过程。这不仅是笔墨语言、个人风神的变化,也寓有山水画观念的变化。其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第一个高峰期的作品,已经抛弃了改天换地式,实际上是生产场景的描绘风气,回归生活的观念很快升华为诗意的形象的表现、人的精神的表现,并与70年代完全进入了人格化时期,使当代山水画的观念实现了从回归生活到表现人格的重大转移。
石鲁主张把山水“当作人来画”“当成个大人来画”,甚至认为“山水画就是人物画”。山水即人的思想,是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深刻思想,也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化,与善于以人的心态观照自然的庄子的观点,与石鲁崇拜的石涛关于山川与艺术家相互脱胎于对方母体,艺术家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从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角度而言,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层的表现。60年代初期的代表作中,《赤岩映碧流》那刀斫斧劈色墨相映的山崖与激流勇进的小舟形成对比,与其说是山川的雄劲,毋宁说是驾舟力量的高扬;《东方欲晓》没有正面表现人,而那富有金石意味的枣树的老枝掩映着灯光的窑洞的格窗,却令人追怀延安赤子们奋斗的日日夜夜。这样的山水是史诗的形象,是人的精神的表现。就气质而言,是阳刚之气、崇高之美、英雄气概在山水画中的流露。另一类作品,如苍拙的老树与湿山嫩草构成的北国之春(《初晴》),如流泉般滚下山谷的羊群的节奏(《高原放牧》、《家家都在花丛中》)的美意,都是有情的自然,都是人的诗思,都是画家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恋情。
70年代,石鲁失去了在大自然中去写生的自由,遂将多年积累之胸中山水凝化为意象,更深地进入了对人生的思考与人格的表现。或以“夜风晓雨湿山花”之景,表达“寄语花丛一语长”之心境;或以《黄河两岸度春秋》为意旨表达他关于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而更多的作品是反复地以华岳松风为寄托,以顶天立地的华岳雄姿一吐胸中之块垒,或在题记中赞其“伟哉宇宙”之盖世雄气,或视为不容恶人贱污之“中国铁打之江山”的象征,或赋以“横眉冷眼镇雄峡”之傲骨,或寄“一手摩天朝日红”之理想,都是他在黑风苦雨压迫中不屈服恶势力欺凌的内心现象,都是他高洁伟岸的英雄人格的化身。这些作品一变60年代初那种浑朴的斧劈兼泼墨并注意墨色强烈对比的热烈画风,有些与书法、人物画同趣,转向钉头般密笔的线型节奏,有些又纵笔挥洒简洁爽快有半空杀纸之势,总体上虽则是由黄土高原为母题的雄阔、厚朴、热烈、转向以华山造像为母题的雄奇、清峻、强悍,甚至不避通常所谓的圭角、露峰等毛病,是其主刚见方的北派山水的进一步强化,是其由寄托对黄土高原的深情转向人格表现的升华。山即是人,石鲁的山即石鲁其人。正是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人文意识、赋予山水画以新的灵魂,也将中国现代山水画推向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如果说集传统笔墨大成表现浑厚华滋感觉的黄宾虹为现代山水第一高峰,李可染、傅抱石通过写生山水回归生活的诗情为第二次观念上的变革,石鲁的强烈的精神性、人格化的山水则是当代山水画的第三个里程,他并且启示了当今注重魂魄和现代构成的新一代画家的第四度变革。
4.花木有心--花鸟画的内在冲动
石鲁的花鸟画创作晚于人物山水。60年代初,花鸟画不多,却颇富新意,尤其以线条拙怪的老藤与红如灯彩的果实构成的《金瓜》等作品,已经显示了他在这个领域里化平凡为神奇的妙思与才华,以及消化和变革传统文人画创造新的花鸟画风范的潜力。70年代初,“文革”中忧愤怨情积郁的石鲁仿佛突然发现了花鸟画这个便于以比、兴之法抒泄情意的利器,遂纵情于兹,其量几冠各类题材之首,并以主观意识的高扬,内在冲动的爆发,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鲜明地区别于60年代花鸟画的风神,成为石鲁后期狂放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鲁后期的花鸟画作品以荷、梅、兰为主要媒介,并将其当作人格和品操的化身,继续着批判会上的批判斗争,或者说诗诬陷迫害中的自我昭雪,都是强烈的、难抑的、真诚的内在冲动的产物。其画荷,或厚腴,或清劲,或烂漫,或凋零,时而叙说“荷花不似一田春”的遭际,时而表现置生死于度外的“淡然”,时而抒发“雨中红粉更鲜娇”的豪气,并不总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传统文人画的思维,因有所感而发,遂得新的精神内涵。其画梅,或在线的转折中造成力的复杂结构,或一枝横挂呈高兰之姿,或仅写一二雪中的花造成奇艳的章法,总之是“写花为诗”,表达“梅为雪而娇,寒宵更放豪”,或“玉龙白雪一天清”的情怀,作为力量、风骨、清气的象征。其画兰,笔总不多,有时仅一二叶、二三花,而构成奇崛,没有丝毫的柔秀,压根就不是兰叶描,而是金错刀,在题跋中或因芝兰思接屈原,或以为觅得了天涯高明,或意在“琢玉于美神”,每一笔都像是杀向“四人帮”之流的利剑。也许缘此,记者多称之为“新文人画”,或誉为当代的徐渭、中国的凡·高,使石鲁画价倍高。笔者并不否定这种历史相似性,但历史的定位却未见得明确的。石鲁纵然与昔日失意文人的抗争有心理同构,且同以喻为“君子”的植物为人格象征,甚至和徐渭、凡·高的精神疾患和艺术表现有着不同的社会根源和反叛的内涵,只有从“文革”大背景着眼,从他的备受摧残的境遇和真理斗士的人格气质以及特殊精神状况出发,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住其内在冲动的深刻底蕴和真诚表现,洞照其内美的光辉和人格的价值,洞照其骤变的时代精神和骤变的表现形式的联系。
石鲁后期的花鸟画不限于“四君子”题材,这位感情丰富的艺术家,在梦魂般的月季花里,在那火红的柿子、石榴里,依然保有理想的热情;在《花卉昆虫录》诡奇的造型和天书般的题识里,痴疯中透析出他对达·芬奇、毕加索、雨果等文化名人的景仰,或画《猫虎镇宅图》以示自卫信念;并画“纵而不颠,奔而信步”的奔马以为自照,都是其情其志的真情流露。虽然仍是对他的笔墨指出过于霸悍、外露的“缺憾”,但也不能不指出正是这种力的刀锋才体现出他的斗争锋芒和不屈的心态,才看得出内在冲动的爆发正化作真诚的心声。在这些并非无病呻吟的作品里,塑造了当代最具忧患意识、自我意识和真诚冲动的花鸟作家的形象,他的内涵、他的思维、他的笔墨和构成的独特性,仍将是花鸟画前行和深化的参照。
5.散我之心--当代书法艺术的怪杰
向来书家对画家的字有异议,从纯书法艺术的角度可以挑得画家字得许多不周,尤其石鲁的字最为刺眼。而石鲁确是书法艺术家,而不是写字的匠人。这种论断基于书法艺术不等于写字,还在于“书为心画”、“书者散也”这些关系艺术本质、艺术底蕴的根本观念。
石鲁早年即具书法基础,从50、60年代画中的题字又可见其于各种书体尤其于魏碑所下的功夫,以及在书法上的悟性。而独立的书法作品则起始于70年代初,就像对写意花鸟的偏爱那样,他又找到了远较绘画为痛快的抒发心志的新的途径,一个半囚、半醒半醉的艺术家,不仅在他书写的文意里,也同样在他新造的特殊风骨中,抒泄他感受到的“万家墨面没蒿菜”的压抑,表现“心怀日月,气感山河”的品格,狂呼“大风吹宇宙,红日照高山”的豪语,或藉书法重申“风格是人”、“艺贵独创,尤贵人品”等言简意赅的艺术观点……文意自思想出,笔意由气质流,并共同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内在生命,这也正如石鲁在他的书法中发表的书论:“书者人之质也”,“风采流芳以为书也”,“画以流美,书以言情”。正因为如此,他仿佛并不考究传统书法在行笔,结构上的美的标准,而着意于自己的情思和气质相谐的线条的节奏,折转的力度,笔墨的量感。其行楷崇北碑之力,方出有圆,更强化其方劲;其草书,不在简化字形,而有意增多折转。总体呈阳刚风神,少蕴藉阴柔,多外露峥嵘。其笔路可氛围苍厚与细劲两类,苍厚者壁画粗浑,方圆相间,细劲者方笔连绵如硬笔所为。者两大笔路又同时演化为漫笔狂书,可谓更野,更狂,更乱,甚而神秘怪诞几不能通篇识读。其书法艺术有时又占去大片的画面,与画,与奇形怪状的“画印”构成一个整体,在综合表现中贯注着诗、书、画、印的一致的风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画家,一位有着真诚的内在驱动力,并使内美与外在形式,人格气质与笔锋节奏相统一的书法家,一位纵情、锋芒毕露、戛戛独造的书坛怪杰。他甚至是一位“笔病”甚重的书家。但也是最具个性风采的书家,也许可以说,他并不是在写字,而是强化了造型性表现,只是藉字的抽象性特质,像心电图那样自然而然地录下自己心灵的脉搏,精神的墨痕,他的书法启示我们的不是写字技巧和方法,而是视书法为心画,为发散胸臆的艺术本质风格,和书法艺术可以更大胆的自由艺术表现的广阔空间。
石鲁作为人过早地逝去了,但这个字却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成为后人永远值得研究的课题。也许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不仅更加珍视他留给世界的艺术作品,也会更加重视他的艺术精神,那些闪耀着真善美的思想和人格的光芒。他试图将社会的立像与个性的艺术风格求得统一的思路;他试图将真诚的深刻的内涵与富有张力的艺术技巧完美结合的心愿,他在传统与现在人间架起的那座大桥,他将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推向现代思维的努力,他在逆境里斗争不已的英雄气概,他为当代中国画的变革作出的贡献……都在他人生与艺术的旅程上,都写在他的艺术风神和艺术理论当中,都写在“石鲁”这两个字之中。
刘曦林
1993年2月于北京
附注
①1943年,石鲁《思想自传》
②全文为:人骂我野我更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人唯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精心动魂魄。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我有心。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冬日的寒凉抵不过大家的热情。 广东美术馆的这个冬天, 因为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