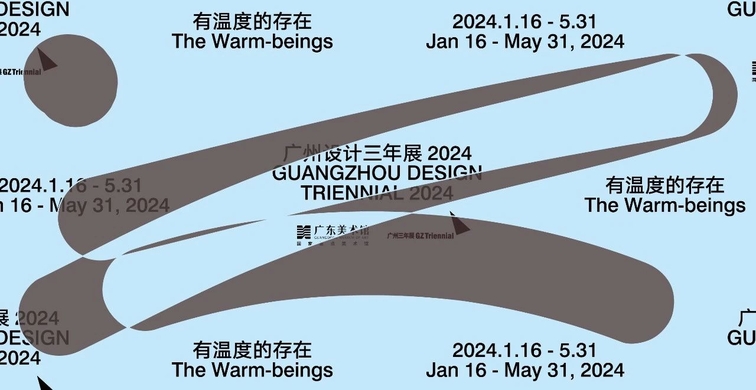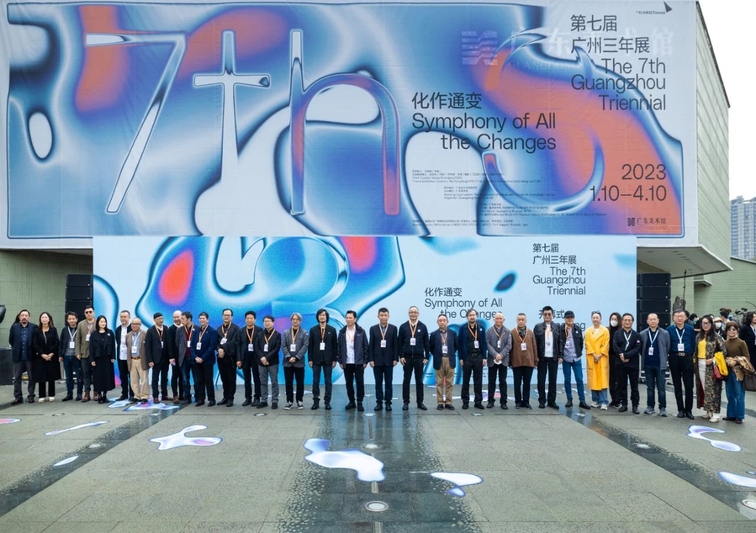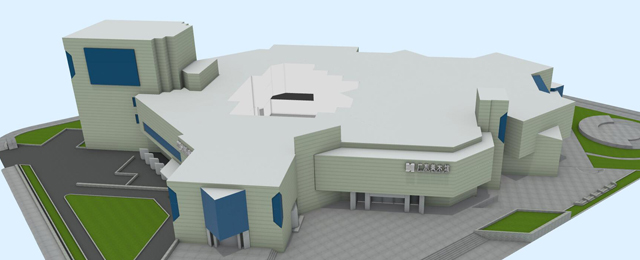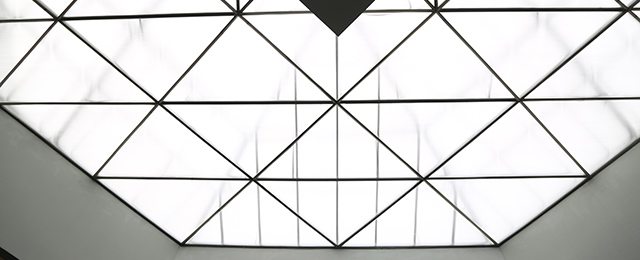多元与同一:策展随笔(陈映欣)
录入时间: 2007-10-25
要在理论上对自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广东中青年水墨作一番清晰的、令人信服的梳理和评判,殊非易事。其难度在于,首先,众所周知的所谓“中国画”和“水墨画”在概念上的混淆不清这一历史悬案,使我们在设置叙述平台时很难在口径上保持某种一以贯之且理直气壮的价值尺度。尽管由于媒材的基本一致性令以上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情同手足,艺术家们也可以在这种暧昧的艺术语境中继续延伸对水墨的个人化理解,但是,水墨语言的多义性和阐述方式的多样性无疑增加了评判的难度。或许,这也正是水墨的魅力之所在,它有时甚至让我们怀疑“评判”的必要性。其二,来自本土艺坛历史背景的水墨语言的功利性,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水墨作为独立叙述对象的个体价值。因之,蛰伏在这种背景之下的水墨因素在真正意义上很难说与原生态的“水墨”这一概念完全重合。相反,在外观上更是时常呈现出同床异梦、各行其是的迹象。虽然说,水墨在宣纸上的涂抹渗化永无可能如天马行空,但是如果我们说本土的笔墨氛围对本质意义上的“水墨”这一概念不够重视的话,我想是不会有太大争议的。其三,如同广东经济、社会形态的斗转星移和观念的日趋多元一样,广东水墨一直以来都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群雄并起局面。当然,我们可以用“百花齐放”这一美好词语来溢美以往的广东水墨。但确实,混沌中偶尔划过的几道闪电仍然无法让我们看清眼前的所有道路。总体来说,缺乏本土水墨底气,忽视群体的力量,未能获得强大的理论支撑等,仍然是困扰广东水墨界的一大痼疾。这是一个众所周知但也无可奈何的事实。
当代广东水墨,直接肇因于以“折衷中西”这一口号为“镇山之宝”的“岭南画派”。据史论称,“岭南画派”这一称谓令其众多传人颇不以为然,原因是这个名字太具地域性,有悖画派创始人的本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岭南画派”诸同仁也曾经对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艺术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它在国内美术界也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但站在艺术本体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岭南画派”的硬伤是极为明显的。以民主革命同路的人身份进行艺术革命的“岭南画派”诸元老,并未能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上为其传人留下足以慑服后世的完整体系。非艺术因素的过分炒作,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艺术规律本身。一句话,先天不足。更严重的是,经过历代的误读和断章取义,其“精髓”便只剩下“写生”二字,外加史论家笔下的辉煌历史。众所周知,一个有生命力的画派至少必须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有比较新颖的艺术观念;二是具备独特的艺术品格;三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四是具备可供发掘和深化的理论资源和技术资源。无庸讳言,“岭南画派”在许多方面是不尽如人意的。当然,在“岭南画派”体系中,出现过多位在中国画坛举足轻重的艺术家,但个体的局部成功在整个艺术大潮中是极其薄弱的,理论体系的缺席更导致了它在当代艺术思潮中面对水墨问题的终极诘问时顿呈失语状态,同时也给再传弟子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令人欣慰的是,理论上的困惑并未能影响水墨艺术家们作为独立个体在宣纸上所做的努力。大部分青年艺术家在经过犹豫和思考之后,终于能够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以客观而坦然的心态来面对师承和地域现实,从脚底下寻找自己的路。针对岭南水墨画坛波澜不兴的学术氛围,青年艺术家们以自己的艺术智慧进行水墨语言的尝试和探索,以求拓展水墨画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参与深度,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早在1980年代中期,一些触觉锐敏的艺术家便开始了对水墨这一传统题材的反思,他们在毕恭毕敬地恪守师训的同时,羞答答地尝试着搞些在那时看来颇为离经叛道的玩意儿。这当中,1986年开始活动的“大阿龙画会”是唯一一个留下名字的水墨群体。“大阿龙画会”的主要骨干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一群青年教师,外加中国画系的几个学生。那时的他们,热血沸腾,胸怀大志,满脑子的叛逆思想,时刻向往着“出走”带来的快感。虽说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过在构图形式上或者水墨的渗化效果上做一些技术性实验,很难说能够在真正意义上认识到水墨本身的文化底蕴,以及如何在技术实验中树立明确的艺术理念并且坚持下去,但应该肯定的是,他们毕竟跨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这种可贵表现在:其一,按照“做了再说”的原则,技术先行也可以作为切入正题之前的序曲 凡事都得有个开端;其二,为真正的实验提供参照文本;其三,借此改变主流权威的价值判断,“锻炼”其视觉承受力,为现代水墨因素在中国画领域的渗透和延伸创造条件。应该说,“大阿龙画会”在以上几方面做到了不辱使命。因此,尽管该群体在举办过影响不太大的一两次展览之后即告无疾而终,我们还是得对它表示由衷的敬意。事实上,“大阿龙画会”只是跃出水面的一朵浪花而已,在以正统中国画形式从事创作的青年水墨画家当中,许多人其实都已意识到必须有所动作,而且有的已经开始“动作”,只是表现得比较“慎重”罢了。变与不变,怎么变,涉及到诸如地域特点、师承关系、个人性格气质、学术理想、价值理念、思考习惯等等因素,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左右着一个艺术家的画笔指向。对于生活、求学于广东本土,直接接受“岭南画派”传人面授机宜的水墨画家来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在外界的冲击下,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固守抑或弃城。如果固守,那么该守住什么?如若弃城,那么怎样确立新的座标?现状是,一部分人身在曹营心在汉,一部分人早已暗渡了陈仓,还有一部分人徘徊在城门口。无论如何,不安分的青年们是不会停下脚步的。继“大阿龙画会”之后,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事件首推1991年“后岭南”概念的提出和接下来“后岭南画派”持续10年的不定期展览活动(备忘:之前及之后,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策划的“星河展”系列展事也为青年水墨画家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舞台)。严格来讲,所谓“后岭南画派”未必称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派,我觉得它更接近于一种“姿态”。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它并未具备一个画派的基本特征。其实,发起人的本意也无兴趣于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画派”概念来诠释他们这个群体,他们更愿意将之解释为“借用”。有论者认为,所谓“后岭南”只是一种文化策略(见王璜生《“后岭南” 一种文化策略》)。笔者同意这个观点。在当今资讯发达、人际横向联系频仍的社会背景下,建立传统意义上的“画派”已经不具有多大的意义,“后岭南”的提出,仅仅是标示一种立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分析在“后岭南画派”历次展览中参展艺术家的人员构成,几乎囊括了活跃于岭南中青年水墨画家中的各路人马,他们操持各种兵器,比划着各种招式“以革命的名义”汇集在“后岭南”的旗帜下。也就是说,“后岭南画派”并非是一个在学术上独立于外界的群体,“后岭南心态”在广东的青年水墨画家中其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不同的只在于有否提出“说法”而已。在此,我们不妨听听该画派发起人之一黄一瀚的说法:“‘后岭南画派’的概念内涵有以下几个基本点:(一)‘后岭南画派’的‘后’字不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前后联系和区别有着相似的意味,更具有后现代多元、综合、全息的内涵……(二)‘后岭南画派’应是对岭南画派的超越,它应直面开放、变革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应直面中国南方社会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所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使‘后岭南画派’的艺术向着艺术反映社会的当下性、即时性的方向转变和发展,接受商业、电脑、新电视流行商业通俗文化对中国画的挑战。与岭南画派拉开距离,与北方艺术拉开距离,与世界艺术同步。(三)全面引进西方艺术样式,在艺术本体的探索中超越岭南画派单一的写实样式,实现中国画在新时期的全面转型。(四)用‘状态’的态度对应北方笔墨中心主义和文人画风,摆正艺术与生活的主次关系,建立南中国清新、明快、率真、内在健康性的美学品格。”(见黄一瀚《多元、综合的“状态”中国画实验区 后岭南画派》,载《当代艺术》总第14期,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黄一瀚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段宣言式的文字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某些个人的价值趋向,但是应该讲,其对于“后岭南”基本理念的表述还是比较清晰和直接的。作为一种学术策略,以一个曾经在本地占据权威地位的学术概念来提起话头,借此提供学术争鸣的空间,这不为一种简捷而实用的方式。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将“岭南画派”作为超越的对象?既然“心魔”早已被战胜,何故还放在心头?如果过分执着于超越某物,那很可能使自己滑进另外一种局限里面去,这个结果将更加可怕。艺术只有“创造”,而并无所谓“超越”。历史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有未来。必须指出,“后岭南”概念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青年艺术家对本土某种积重难返的学术惰性的强烈不满,也是一段时间里相对沉寂的广东水墨界闪烁的一个亮点,其纲领具有比较明确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但是,虽说“矫枉必须过正”,我们也必须警惕:概念上相对狭小的地域针对性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血气不足和虚火上升。考察广东青年水墨界的现状,把“理论”抛给理论家,埋头手上的艺术实践,在踽踽独行中寻找自己的水墨感觉,这仍然是广东大部分水墨青年的行为方式。它较符合广东本土勤奋务实的一贯作风,代表了大部分青年艺术家的普遍心态。同时,他们也对目前国内水墨画坛的走向保持谨慎的关注,更珍惜每一次的展览机会,这又在某种角度上折射出广东文化善于兼收并蓄的传统特征。
有两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自1990年代起,陆续有多位外地水墨艺术家因工作关系落户广东,他们在国内以至国际水墨艺术圈都已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再就是若干位早期在本土具有一定知名度,而后远涉重洋出国深造的艺术家重新回到广东的高等艺术院校任教,回归国内美术界。两者相加的人数,在目前广东地区较高水平的水墨艺术家群中占有不小的比例。他们的加盟,一是加强了广东水墨画的群体力量,二是改变了广东水墨界的基本格局。第一层意思是不言而喻的,而第二层则更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那就是打破了岭南水墨界的既定局面,即“岭南画派”再传弟子一统水墨画坛的状况。它一方面激活了本土水墨画坛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阻止了由于“近亲繁殖”造成的“品种退化”。大大有利于打破既定的学术秩序,并使广东水墨界的重新整合成为可能。况且,这些艺术家彼此之间的学术倾向互不重叠,个人风格也颇为强烈,对丰富广东水墨图式和水墨理论有着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另外,他们个人在外界的学术活动和与国内、国际各方面的联系,也将有利于扩大广东水墨的影响范围。
而在广州以外的各级市县,同样也活跃着一支支不可忽视的水墨队伍。尽管由于地理因素的关系,他们未能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水墨主流圈,但作为个体艺术家,许多人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不亚于广州艺术家的技术水平和思考水平。他们也是广东新水墨画坛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按上述情况看来,目前广东的新水墨画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看似无序的准自然生态。在这个生态圈中,前卫与改良并存,群体与个人互为补充,大家都在各自的空间里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广东新水墨的本质是什么?它未来的演变态势将会怎样?对此,妄下结论无疑是不明智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广东美术馆策划这个展览的目的,正是旨在为关注广东新水墨画的有心人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参照系,并企望各方的有识之士多多出谋献策。
三
大体上划分,这次展览的参展作品可以分为抽象水墨、具象水墨,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半抽象水墨三大板块。这种划分方法当然未必中肯 具象作品中可能包含着抽象因素,反之亦然 但至少在外观上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较为直接省事的言说方式。
抽象水墨作品在图式语言上较多地借用西方艺术的抽象形式,但在意味上却呈现出浓厚的东方情感,其哲理因素比起画面的绘画性份量要重得多。这一路的艺术家有石果、方土、刘子建、魏青吉等。石果的作品蕴含着极强的理性成分,技法语言在严谨、单纯的表象之下透射出尖锐的矛盾意味,雄强和阴柔完美的统一使其作品具有一种“横贯东西”的象征性;方土则把代表影像时代的光碟(CD)造型融进他素来挥洒自如的淋漓墨气之中,以清晰的语言表述了一种文化对比方式;刘子建在他的作品中以神秘的纵深感、不明漂浮物的无序感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制作技巧活现了后物质时代无所不在的欲望放纵。以秉性平和的水墨作为媒材更使之平添了一层反讽意味。而魏青吉似乎更未敢忘怀诗意的表达,在极具宗教感的庄严结构下,别出心裁的轻快符号让我们时有惊喜。
黄一瀚、周湧、郑强、左正尧等人的创作则与流行的城市文化息息相关,对都市题材的敏感令画面的当下性以及文化针对性显而易见,较好地解决了以水墨媒材表现都市题材的技术问题(以黄一瀚、周湧等人为代表的“卡通一代”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特别是南方消费文化的一个经典符号。水墨只是他们使用的多种媒材之一)。
马文西、陈文光、关玉良在整体图式上沿用传统水墨符号,但在笔墨素材的运用上体现出纯粹的个人化倾向,情绪语言淋漓尽致的发挥是他们作品的重要特点,作品散发出浓烈的笔墨魅力。其中马文西、陈文光对日本绘画材料的使用令作品增添了一种别样的气息;关玉良的作品则在漆黑而平整的外表下涌动着一种悲壮的英雄情结。同样,素以山水画家身份出现的张彦,这次以矿物颜料制作的重彩抽象作品亦令人耳目一新。
李东伟以中国传统青花器皿植入山水之中,看似突兀的素材组合在重墨的皴擦罩染之下令画面横生一层沉郁的时空感和历史感,其演绎哲理的手法颇为直接而贴切。黄国武、唐力、何枫、卢小根、崔跃等虽然都以人物为表现题材,但切入点和画面意趣彼此却截然不同。黄国武的创作一直对技术眷顾有加,这次的参展作品,既显示了其扎实的写实功底,也显示了他企图穿越时空,通灵于古人的良苦用心。唐力笔下的人体则形随笔走,在闪展腾挪的瞬间让我们饱览了画家的激情和机智。何枫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女性特征,手法虽然简约,但温情而细腻的乐思足以让我们回味平凡人生里拥有过的美好时光;卢小根画中的人物则沐浴在一种闲适情景中,漫不经心的笔调活现了都市生活可爱的一面;崔跃让他作品里的人物笼罩在一片迷惘情绪当中,都市少女在山水间漫无目的的游荡似乎重现了现代人日渐朦胧的山野之梦;而苏百钧花鸟画的情思细腻、方向山水画的温暖和煦,林若熹人物画的奇思怪笔,令这三位以明显的写实风格为表征的艺术家散发出别样的风采,他们之间具有某种比较价值,同时也以不同的画面效果使我们对在水墨界屡受诟病的“写生”一词有了更为乐观的理解。
李劲堃、庄小尖、张东、陈映欣的山水画,则以较为明确的山水“格式”毫无掩饰地倾诉内心深处的山水情结。李劲堃的雄浑深邃、庄小尖的奇郁沉雄、张东的纯净剔透、陈映欣平实中的苍莽,着眼点虽各不相同,手法的差别也比较大,但对山野气息的深情均溢于言表。
在以“花鸟”为参展题材的艺术家中,苏小华的纤巧灵秀、安林的神秘迷朦,还有林蓝的致力于撞粉技法与装饰性的结合、陈太一的以正统大写意技法融入“场景写意花鸟”的努力,也显示了各自的才思和技法美感,相映成趣。
四
水墨作为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古老艺术,在当代所面临的困惑比起其它艺术品种(特别是新媒体艺术)显然要大得多,肩上的负载也更为沉重。其两难之处在于,如果我们仅仅将其视为材料学意义上的一种绘画体裁的话,那么问题将不复存在。但试想失去了本土文化意义和传统积淀,对水墨画来讲将意味着什么?而倘若我们仍然视之为东方民族的一种话语方式,一种崇尚内省的精神附着物,那么它和世界其它文化的沟通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早在上个世纪初叶,我们的先辈们便已经开始了这种思考,但若以为问题如今已经完全解决,尚为时过早。事实上,迄今为止水墨在国际艺坛上仍属边缘艺术,仍然未能跻身国际文化主流圈。如何以本土的方式取得与国际大文化圈的对话权,无疑是我们作为后来者的责任,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课题。近年鹊起的“中西文化比较学”,正是着重于研究中国文化如何在与世界其它文化的比较中调整自身的方向,以适应世界一体化的大文化结构。对于作为文化领域组成部分之一的水墨艺术来说,我们不奢望它能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但拓展其话语空间,使之成为具有当代性的、对当代生活具备起码发言权的一种文化消费品,无疑是水墨在当今时代获得身份认同的先决条件。否则,有朝一日,水墨画在当代文化界的视野中彻底消失将不再是一种假想。几十年来,中国艺术家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效果是显著的。作为在近代思想史上多次领风气之先的广东,我们的艺术家们也未曾懈怠,他们以自身对水墨的理解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激进,也有温和;有立足现实,关注当下,也有神游天外,在当代都市的浮躁中保持一种永恒的人文关怀情感。水墨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语言的随机性和情感的个体特殊性。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语言的多样化未必是一件坏事。“大阿龙”也好,“后岭南”也好,“外来派”也好,纲领可以确立,话题可以扯大,口号也不妨多喊几声。但我想,跳出狭小本位,在大文化意义上找准“水墨”的位置,确立同一性,承认多样性,因应传统,立足当代,解决水墨当下性的具体问题,才是广东新水墨的希望所在。
一瓢墨汁倾注在宣纸上,幻化成一个玄妙而缤纷的世界。我们因此钟情于水墨;我们也因此背上了责任、背上了困惑,然而我们从未怀疑:脚下的路,是走出来的。
(本文为配合展览“现象:‘后岭南’与广东新水墨”专题研究文章,详见《展览出版典藏档案》。)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
冬日的寒凉抵不过大家的热情。 广东美术馆的这个冬天, 因为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