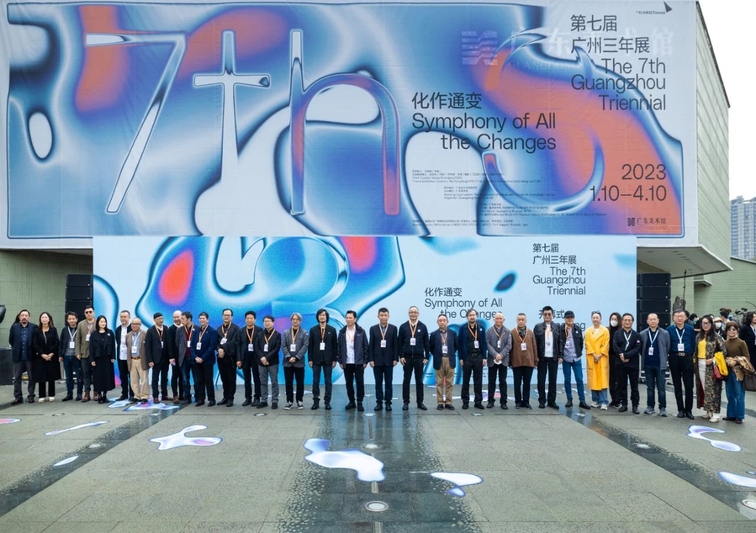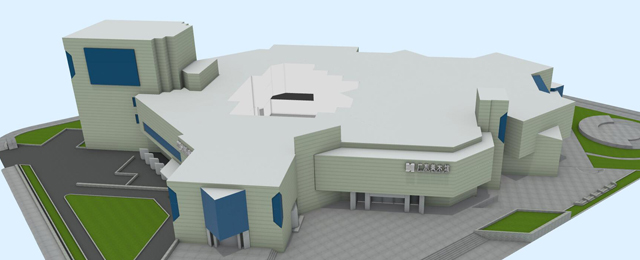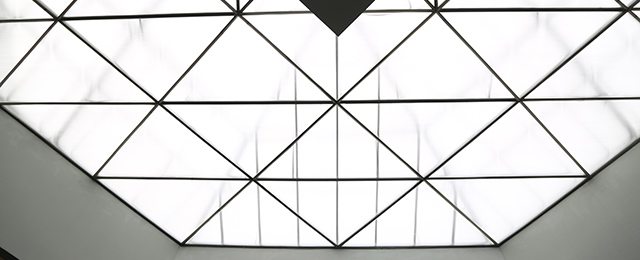危险的边界与空间,危险的愉悦—王璜生“边界/ 空间”展简论
录入时间: 2018-03-29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为什么我要在行为中加热油脂?它们会很轻易地融化开,那么此刻油脂角又在哪里呢?我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一个关系中来思考,马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真正的政治……没错,这肯定会激起大家的愤怒,那么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就会产生讨论。—约瑟夫·博伊斯《什么是艺术?》
关于《王璜生:边界/ 空间》展览,下面这段概括性的表述比较简洁,并且提出了一些关键词:“他的艺术创作,经历了从传统水墨向当代艺术转换的探索历程,夹杂着传统文人的品性修养与突破自我的独立不羁精神,以及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现实及历史议题的深刻关注和介入态度,使其艺术创作不再是对高雅文化和视觉愉悦表征的调用,而是通过对文化记忆的重建,重新审视全球背景下政治与多元文化的现实,并让人们对当下现实的某些僭越行为有所警惕。”[1] 转换、关注、介入、文化记忆、审视、警惕……,这些关键词的意念的确在整个展览中不断呈现出来。该展览策展人巫鸿则更为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当代艺术总是立足于现下瞬间去探索超出经验领域的未来,它赋予自己的使命总是突破现存的视觉语言和观念的边界,去开拓艺术表现中的新的空间。王璜生的艺术实验充满对边界与空间的探寻和质问。如果说‘边界’的传统含义离不开线性界限的意象,王璜生的线画和线的装置则通过打破这种意象显示出线与空间互动转化的新的可能,从而成为对视觉艺术当代性的一种表述。他的抽象艺术总是具体和实在的,既从观念的反思中也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怀中获得生命。”[2] 这里有对“边界”与“空间”的多重概括性表述:从当代艺术的使命到对王璜生艺术实验的表述,再具体到在展览中的线画与线的装置所体现的突破与转换,最后归结为在抽象与观念中的具体、实在与生命。从中可以启发观众和批评家从展览的抽象艺术特征中思考其主题内涵。从整体性的思想深度和创作力度两方面来看,我认为这次展览大大超越了王璜生以往的个展,较为全面地显示出兼美术馆长、策展人、艺术史论学者和艺术家于一身的王璜生在当代艺术创作领域中所具有的内源性爆发力与跨界潜力。当这个展览呈现在观众、艺术界、评论界面前的时候,各种不同的阐释角度、立场和评论都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在具体作品中折射出来的问题意识与图式语言的选择及表达,试图“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在一个关系中来思考”(约瑟夫·博伊斯),试图在不同层面和维度上回应 “边界/ 空间”、记忆与现实等这些当代文化的关键概念所带来的紧张思考。
一、关于“边界”与“空间”
这个展览是充满主题性的,并且蕴含有尖锐的问题意识。所谓“尖锐”,既有指向理论思考的锐利探索,也有面向现实维度的敏锐关怀。“边界/ 空间”,不言而喻的是,这两个概念有内在的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核心概念的不同表述。在物理学的意义上,没有边界,无所谓空间,反正亦然。在社会与人文的意义上,“边界”与“空间”的内涵变得非常复杂,文化、政治、心理、审美等等因素都可以在“边界”与“空间”中找到繁复的表象和更加多元的表述。那么,谁的“边界”?谁的“空间”? 除了物理学意义上的“边界”、“空间”之外,属人的“边界”、“空间”是如何形成的?从国族到社会,从集体到个人,从法律到伦理,从应然到实然,所谓的“边界”和“空间”均有多种生发场域、多种观察维度和多种表述语境。“边界/ 空间”是该展览最为凸显的主题,但是“边界”、“空间”也是时下当代艺术展览中并不鲜见的标题或符号,那么如何认识王璜生的“边界/ 空间”作为一个主题的独特性?所谓“主题”(Theme)往往是指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核心论题及由此而表达的首要观念,它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它以题材内容、表现形式、艺术语言等要素作为外部呈现方式而表达出来,并通过观众的观赏、思考而获得意义。从该展览的各部分构成及整体性而言,其主题显然是相当明确的,如策展人巫鸿在前面所言,王璜生的艺术实验充满对边界与空间的探寻和质问,是对视觉艺术当代性的一种表述:“王璜生的抽象艺术因此总是具体和实在的,既从观念的反思中也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怀中获得生命。”(同上)“对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的隐喻”,“既从观念的反思中也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怀中获得生命”—这就是蕴含在这个展览的作品中的主题与意义,王璜生以创造性的视觉手段表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关怀。
在消费主义时代碾压一切的时候,不应被遗忘的“边界”与“空间”只有在当代艺术中才能被拯救出来。这批作品的创作过程无疑都渗透着某种观念的指引,这与当代艺术的创作思潮是一致的,这些观念无论持有何种价值诉求,其共同特征是把艺术内部的语言实践与外部世界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从这两方面的张力之中实现当代艺术之于生活世界的真实意义。在“边界”的多重含义之中,从传统中国画到当代艺术的装置之间显然是“边界”之一。这里发生的是传统的断裂、转换和新的诞生,焦点是“线条。它的出发点当然是中国传统艺术,是王璜生作为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国画家笔下的线条,是积淀着个人文化习得的强大基因,也是古典文化与民族性混融一体的文化象征,这一出发点的意义不可低估—它预设了探索性转换的价值、意义和难度,作者把从传统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换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展览中讨论类似“当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的关系”这样的议题,但这不是该展览所带来的核心议题,因为在我看来它的重点不是从传统中突破,而是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跨越边界。从覆盖着纸媒上的线条到铁丝的线条形态和以光影晃动在墙壁上的线条,从笔墨下的线条到物质化的线条再到出现在拓印复制中的线条,在其中推动和引领着这种转换的更多是面向现实的精神性、社会性的因素。他以“线条”为起点,以“边界/ 空间”为定向场域,以多种媒材和手法为操作方式,在实现了语言转换的同时也生成了富有思想张力和文化内涵的隐喻关系。
二、线条的转化与隐喻
展览中的《游·象》系列在王璜生的创作发展中是带有转折性的节点,本文的作品论述也由此展开。作者自述说:“《游·象》系列一直追求和表达的是自由与控制、表现与修炼之间的互为张力,中国的笔墨与线条,讲求的是修炼和手腕的控制,而线条的表达却趋于自由精神的张扬和随心所欲的书写,我希望在这样的制约与突破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并延伸为一种审美的力量。因此,《游·象》体现了东方古典意趣与现代自由精神的双重表达。”[3] 如果作者止步于此,这将是向抽象的笔墨线条王国继续出发的台阶,从目前的审美效果也可以预设其未来的发展可能。但是,最关键的一种转折同时在这里出现:“在《游·象89》中,我发现线条与铁丝网存在一种很强的对应关系 。之后我开始使用铁丝网做作品。”[4]其实,在这种“发现”的背后还潜藏着精神上的内在线索,未必仅仅是发现了线条与铁丝网之间的对应关系。巫鸿先生对此种转变的内在原因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王璜生的作品因其连绵流动的线条而富于诗意的抒情,但也通过流动的不稳定性激发出心理的紧张和对转化的焦虑。这种紧张和焦虑被一些关键细节放大,使抽象的线成为对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的隐喻。”[5] 这里可以结合王璜生的自述来分析。如果说对转化的焦虑和紧张感还是源自对古典线条的抒情传统如何融入当代艺术的思考的话,那么王璜生自述中的“发现”恰是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转化契机,线条与铁丝网之间的对应关系使他找到了“一些关键细节”,“使抽象的线成为对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的隐喻”。当然,这个“发现”的依据只能从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价值关怀中寻找。
《线象》系列是王璜生从古典艺术的线条迈向当代媒材艺术中的“线条”过程中的一级台阶,是一次“越界”行为。就媒材的选择而言,以报纸取代宣纸当然不是“纸”的选择问题,而是文化基因的重新选择,是彻底改变古典“线条”的安身立命之处的颠覆之举。那么,接着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对被选择的“报纸”是否也有选择的问题?在目前我接触的资料中没有看到作者自己的相关说明,在我看来恐怕很难说没有选择,但是应该没有非常刻意地选择。前者涉及创作态度,后者则是动机问题—无论是《南方周末》或是《参考消息》,看来都是一种比较随意的选择结果。没有证据表明作者试图让被选择的报纸上的内容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更难以论证覆盖在报纸之上的“线条”是对报纸内容的“介入”。真正的“介入”应该是脱胎于古典意味的线条对新媒材的介入,是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介入”。我不否认在观看这组作品的时候我曾经掠过一个念头:在线条之下、之外的文字内容是否也有某种看头?但是在试图细致地、检索式地观看作品之前,基于对作者的了解就使我马上否定了它。在这组作品中,各种文化的、政治的寓意只能通过间接迂回的审美方式表达出来:被奔突的线条与漫漶的色彩所反复涂写的报纸文本已经难以按正常的方式阅读,但是由标题、关键词、影像所组成的文本内核仍然存在,原生文本与后发的图像之间所形成的冲突反而衍生出新的视觉文本,一种介于文字阅读与图像感受之间的视觉冲击形成了新的话语力量。
但是,这组作品与那些在海报、广告牌、公共告示牌等平面上植入主题性的文本—如珍妮·霍泽尔(Jenny Holzer) 创作的《常理》(Truisms)和《煽动之词》(In flammatoryEssays)等作品[6] —不同,王璜生并没有打算以文字表达作品的主题信息或政治动机等,而是试图把观众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在文字与图像(由单纯的线条和色彩构成)的层叠关系中。在这种相对抽象的语境中引发人们对于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张力的思考,而不是直接以图像中的文字表达政治观念或价值诉求,这既是对于言论语境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同时也包含有更为深刻的思辨性。
如果把王璜生的“线条之转化和隐喻”作为一个议题展开的话,除了从线条到铁丝、从宣纸到报纸的转化以外,还有第三个维度:媒材与制作方式中的纱布和拓印。
在《墙》(纸上作品)中,“由一条条纱布的印痕组成,隐喻着伤害、痛感、隔离、流血、呵护、疗伤等,而纱布拓印本身的肌理特质及墨色深浅干湿的表现效果,构成了内涵丰富而具有力量的视觉表达。我力图用尺度较大的画面,与微妙细致的拓印痕迹包括纱线散乱的印痕,追求视觉与心理两重层面的体验性表现。”(艺术家自述)离开了笔锋建构的线条,以物理性的“印痕”所造成的肌理效果和色彩效果完成视觉与心理感受的体验性,这当然是另一种方向的转化探索。与此比较接近的是2016 年新创作《痕·象》系列,其中“纱布绷带线头的印痕与水墨的渲染,及与报纸、宣纸之间的现实和文化信息等,构成了对伤害与保护、修复与升华等的隐喻。细腻、脆弱、敏感的印痕,与画面纵横恣肆流动的线条块面及墨团水点,形成丰富而微妙的对比性语言。这一些无不流露着我对现实与生命的一种特别关注和关怀。”(艺术家自述)在《箴象系列》中的鲜红的纱布印痕具有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那种纵横、斜穿、重叠的动势和渗化着的红色可以在某些观众眼中猛然激起对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
本来就是抽象的线条在经过上述三种维度的转化之后完全脱离了古典形态,成为当代性的艺术语言。在这里不再是那种以自我表达为中心、以自发和偶然为姿态的完全自由的艺术创造过程,而毋宁说是从符号学的意义上把线条的抽象转化为观念的揭示、冲突及其记录。创作的主题动机已经被置于某种文化记忆的语境中,只有抽象的语言才得以完成具象所无法胜任的工作。假如说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把国旗、箭靶、尺子等生活中的物像描绘为“一幅画像从具象返回到抽象”的过程的话,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所关注的不再是物像的再现或符号背后的意义,而只是希望通过绘画的制作思考绘画的性质与边界;他的问题意识始终是指向绘画的本性。那么,王璜生的抽象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抽象的线条背后始终关注着符号的意义关怀。面对全球化时代语境中的政治的种种奇诡、颟顸和粗鄙的文化特质,这种以抽象的符号意义表达以文化记忆为中心的问题意识是一种相当理性和智慧的策略选项。我们也可以把这里的抽象线条、色彩作为一种“显性文本”,通过还原生命经验而对这个抽象文本进行“症候式阅读”,即在“显性文本”中出现的各种症候(如尖厉、缠绕、无序、机械等)中发掘其隐含着直逼“边界”的“隐性文本”。
三、有关“边界”叙事的装置及其符号
《界》(装置、影像,铁丝网,2017 年)是为本次展览而创作的新作,从形式上看无疑是整个展览中最具有全方位的感受冲击力的作品,而其主题和意义也是整个展览中最能体现“边界/ 空间”的极限性质的重量级之作。
作者的自述表达了一种宏观的意义动机和对审美效果的预设:“《界》这个作品是对当下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历史问题所做的思考与创作。在这个创作中,我希望有更为宏观、更为本质性的表达,因为我认为人类就是在这种逃难、紧张、向往、死亡的过程中存在着的。摇晃的铁丝网架、铃铛的响声、海浪与跑步紧张急促的声音,使整个作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让公众产生更多的联想和心灵上的冲击。而对于我接触过的逃难、难民等历史记忆,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宏观的视野与本质性的表达使这件大型装置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内涵,在“人类就是在这种逃难、紧张、向往、死亡的过程中存在着的”这句话的表述中包含有作者原初记忆与生命体验。作者在接受访谈的语境中进一步敞开了记忆的场域:“当下世界不安的现实如战争、逃亡、难民、越境等,引发了我少儿时期以来的记忆及曾经的耳目经验,六七十年代地处南方海边的家乡,时常接触到‘偷渡’的时事和故事,以及有相关经历的人,其场面感至今仍历历眼前。而当年自己也差点被‘好心’的兄长‘暗渡’了。‘界’,既可能指向于边界、区域、边境,指向于挣扎与奔突,而也可能是生存及精神的另一种向往和境地,一种恒永的境界。”[7] 这是一段个人的历史记忆,是作者内心最真实的生命体验,这对于深刻理解这件作品至为重要。事实上这是生活在南方沿海地区的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是那段青春岁月中的禁忌图腾,至今仍然是主流历史书写中的盲区。我曾经在非历史研究文本的写作中记录过我当年耳闻目睹的一些“偷渡”史实,但是难以传达出那种真实的心理氛围。
在中国当代艺术文本中,《界》可能不是唯一涉及这个主题题材的作品,但可以说它是最具有心理和审美震撼力的作品。从记忆到审美表达,最后回到现实与历史的对话,艺术承担了通过揭示创伤来疗治创伤的作用。巨大的、层层叠叠的、而且是摇晃的铁丝网架,海浪的声音与风中铃铛的声音,奇诡的光影,观众在作品面前无法抗拒地感受到现场气氛的恐怖与不安,“边界”的真实含义极端尖锐地呈现出来。在这同时,穿行在作品之中的观众也会被激发出对生命意志的领悟,从恐惧中催生的审美反抗成为这件作品最后的音符。不应忽视的是伴随着视觉冲击力的声音所传达的心理记忆,它是与人的呼吸更为直接呼应的节律。约瑟夫·博伊斯在他的《首领—激浪之歌》(1963 年哥本哈根、1964 年柏林)中充分运用了声音的元素,通过和人一起包裹在毛毡里的麦克风,博伊斯的呼吸声、咳嗽声和尖叫声和他制作的模拟兔子与牡鹿的声音在展场回荡,同时传到外面的大街上,博伊斯以此表达战后柏林的战争记忆和伤害经验。在这里应该谈到的是,王璜生对博伊斯的艺术和思想有过深入接触,曾经于2013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成功地策划了“博伊斯在中国”的展览;他对于博伊斯“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同时也作为一种艺术的独特行为及形态”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巨大影响深有体会。[8] 我认为博伊斯的社会关怀、政治意识和具体到伤害、记忆、治疗等议题中的深刻隐喻,都对王璜生的创作信念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召唤与影响,就如他自述“博伊斯那件《革命就是我们》的照片作品上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坚定迈进的步伐身姿”对他产生的强烈感染力。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也可以把《界》(当然还有《谈话》等作品)看作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向博伊斯表达敬意的探索之作,是德国“巫师”之音在红色中国激起的又一次回响。
如果在迄今为止的当代艺术展览目录中检索“铁丝网”与“纱布”,不难发现王璜生对这两种物品的运用并非首创,但是从组合的方式、作者的主题动机以及背后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来看,可以说他明确地建立了自己的叙事主题和隐喻关系,使他的作品有力地逼近“边界”。《缠》这件作品显然蕴含有某种特殊的意味。缠绕在铁丝网上的纱布、在其下面的鼓风机、被光线打到墙上的线条光影,并不复杂的装置产生了强烈的感性力量。从中可以看出有两个迅速转换的审美感受过程:从物质的经验感受(铁丝网、纱布、风机)同时性地转换到视觉、听觉等身体感受神经之中,然后从感性又迅速蔓延到精神的层面,在这里依赖观众的生活经验和内心精神生活的储备而产生不同维度的审美感受。本来,以上所说的感受转换过程也是观看装置艺术的一般审美过程,但是这件作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所选择的物质媒材所积淀的特殊含义。
被撕裂的纱布作为一种视觉符号,以及铁丝网的倒钩尖刺所激起的想像,都涉及到生命经验中的“疼痛”的符号化问题。作者自述说:“当我用纱布轻轻地缠绕着铁丝网,手与身体与这蒺藜芒刺相接触,纱布在缠绕包扎中不断被扎破被撕裂,同时还被火灼烧着,这时,自己为这样的过程而深深触动和感动。而当微微的风吹动凄美的纱布飘散在铁丝网间,或强劲的鼓风机吹起纱布撒向空中,也许,可能会产生一种包扎、癒疗与伤害、疼痛相杂糅冲突的矛盾与张力。”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相当重要的关于“疼痛”的创作经验。当代艺术表达“疼痛”的方式更多地是通过符号化与仿真性而实现,这使不少人受到迷惑。波德里亚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符号学、政治经济性与消费社会学的结合,他引入符号学的最后结果是把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看作是不断失去现实性的符号体系,消费者本身也失去了主体性,一切都被符号化了。当代艺术是否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他更进一步地从多方领域阐述了他影响极大的“仿真”(simulation)理论。他指出日常生活现实已倒过来成了一个模仿的过程和虚构的过程,或者说,再大胆的虚构也无法与现实相比;现实与虚构的逆转关系就如同现实与语言的关系一样。波德里亚认为物品必须首先要成为符号才能被消费,因为只有符号可以出现在广告之中,只有符号才能被人们所言说、所推崇、所理解。这样一来,是符号建构了消费品的现实性,现实反而成为了符号的附庸。因此,“疼痛”也只能以疼痛的仿真形式出现,“疼痛”的符号化并无法真的消解了“疼痛”的痛苦。那么,《缠》的铁丝与纱布作为“疼痛”的符号既是一种仿真的想像,同时也是隐含在生活之中的“疼痛”记忆。
《谈话》从制作手法来看正是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流行的挪用(appropriation)艺术方法,例如杰夫·昆斯(JeffKoons)创作的《兔子》(Rabbit,1986),以高超的不锈钢工艺模仿消费社会最常见的玩具气球而隐含着对于这个社会的揶揄和批判。但是《谈话》是一组内置铁丝网的沙发,把铁丝网和沙发组合在一起,并且形成事物外表与内部的紧张冲突,最后上升到“谈话”这个主题,从而使作品被置于极为敏感而尖锐的边界。《谈话》对物品的挪用和改造是在强烈的思想动机引领下实施的,艺术家自己的阐释极为精准而深刻,必须完整地引述在这里:“我一直在思考舒适和尖厉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现实,表面上看,比以前好很多,也似乎舒适多了,但是,又有好多东西很纠结很揪心,说不清楚,这种感觉一直很强烈;而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做出一种东西,看起来很平常,但是里面要有转换,从视觉到触觉、从感受到思维等。比如做这个沙发作品—《谈话》,沙发本身跟舒适有关,看起来很简单,很舒服,很日常化,但其实它冷冷的黑黑的硬硬的质感,而且透明的,显露出内里的尖利铁丝网。这使人在视觉和感受上产生强烈冲突。而“谈话”的命名也很平常,似乎是我们日常中经常做的一件事,但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谈话”就如“喝咖啡”一样,是有特定而模糊的涵义的,在这样特定而模糊的涵义背后,是一种特殊的生命经验和感受。”(艺术家自述)这是关于作品与时代关系的深刻表述。“舒适”与“尖厉”的物质感受对比,光滑、舒适的表面与钩缠铁丝网的内里所构成的强烈心理冲突,而且这样的沙发不止一件,散落地放置在一个阶梯空间之中,沙发本身的危险与空间中的不稳定与反复性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悬疑与焦虑的世界。在这里,沙发与铁丝网的存在是一种对话结构:安全与危险、舒适与痛苦、平静与波澜的对话,这样尖锐冲突的对话结构强烈地提示着“谈话”这个主题中的不祥之兆。关于“对话结构”,这是整个展览的表述语言的语法特征,将在下面再作论述。就这样,《谈话》的视觉对比成功地转换为对某种生活经验的强烈隐喻,而这样的转换和隐喻来自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情境”和“特殊的生命经验和感受”,这也是整个展览的思想底色。
上面的自述中从《谈话》很自然地延伸到“喝咖啡”,有“特殊的生命经验和感受”的读者则不难继而延伸到同样具有“特定而模糊的涵义”的“喝茶”、“旅行”等生活景观。这件作品的艺术手法从所触及的理论问题来看,它是非常符号化的。符号学(semiotics)在当代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帮助艺术家把视觉经验转换为代表着真实语义机能的符号,通过这种转换使视觉经验成为符号意义,于是视觉经验中的“沙发”和“铁丝网”经过冲突性的聚合而转换为特殊的“谈话”符号。的确,在当代公共生活中有许多特殊、暧昧、敏感的景观有待在艺术中被重新发现和表述,中国当代艺术如果不想匍匐于当代西方艺术的视觉经验与原创性之下,就必须在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发现问题、提炼主题和探索边界。
从这组作品中引申出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是,在现实中有许多活生生的事件、经验、观念不被进入记忆,发生与遗忘几乎同时发生,需要抢救的不仅仅是历史档案,更有现实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谈话》的独特价值,它不是在当下对历史记忆的钩寻,而是为在未来日子中钩寻历史记忆准备档案与素材,今天的艺术家就这样与未来历史学家联手抗击着从今天蔓延到未来的遗忘之神。
从记忆心理学的原理来看,暗示与记忆有着隐秘的联系。图像对记忆的暗示作用会使人心领神会,尤其是在空间极为有限的文化语境中,有暗示作用的图像是一把锋利的小刀,在人们的视觉记忆中悄悄地划开了一条危险的裂痕。当然这也必须依赖观者或记忆者的知识背景,假如在一幅静物画中有浴缸、垂地的床单、鹅毛笔、写字柜、墨水瓶和纸条,被列为禁忌的法国大革命的形象难道还不呼之欲出吗?
在这个展场中无论只是匆匆一瞥还是反复观看,我相信留在观众记忆中的印象是强烈的,而只要稍微把印象梳理一下,线条、铁丝网、纱布、沙发等视觉形象马上会带着强烈的符号特征而进入记忆。符号从物象中被提取出来是因为它呈现了事物的意义,艺术家之所以选择某种物象也是因为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尤其在装置艺术中,物象—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对于主题的展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符号的恰当运用涉及到主题意义与表述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王璜生对该展览中的符号运用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在这个展览整个策划布展过程中,我和巫鸿老师反复讨论各种问题:有些符号是否太强,有些问题是否太突出,特别是像铁丝网这个符号会不会太直接太强烈之类。”(王璜生在展览研讨会的发言)直接、突出、强烈既可以是一种追求,也可以是一种禁忌,在两者之间必须依据不同的言说语境把握恰当的“度”。王璜生自己对“度”的把握是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来思考:“第一个方面是强调体验性。无论是纱布铁丝还是宣纸笔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比较重视其中所蕴含的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我想使这些材料内涵与生命本体发生关系。我希望这种感觉能传递给观众,观众走进展厅看到铁丝网会有某种特殊的感受。第二个方面,我对一种材料的选择有时候带有一种现实情怀;……所以作品创作首先强调材料本身的体验性,材料质地的指向或者其表征性、表意性,应该与我的体验性相吻合,才能被我所选用,我希望按自己的感觉去做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发言)体验性当然是属于个人的,把它作为对符号选择及表达程度的解释是对意义禁忌问题的淡化、转换和悬搁,把观众的接受问题引向审美体验问题,“微妙的感觉”和“体验性”可以有效地缓解符号的紧张感与对抗性思维。
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哪里有危险的“边界”与“空间”,哪里就有危险的愉悦,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种诱惑是极为美丽而又脆弱的,正像王璜生对展览中的《溢光》这件作品的自我评述:“流光溢彩,是一种何等美丽而辉煌的想象。我希望用晶莹剔透的玻璃管与闪烁光芒的铁丝网,以及通透晶亮的光影,构建一个‘溢光’的场景。当锋芒的铁丝被挤压穿过脆弱的玻璃管,玻璃的碎片散落满地,闪亮而缤纷,似乎,这其中有一种生命与现实的隐喻与张力。”这无疑是关于危险与愉悦的隐喻。
四、“艺术世界并不是孤立的世界”
在把个人的公共关怀推进到“边界”的经验中,必然伴随着不少道德勇气的受挫感,这种感受必然渴望得到理解和认同。在面对真实的经验世界的时候,需要艺术家有真诚和敏锐的思想品质,所有的艺术修辞都是为了表达而不是遮蔽这种经验。在任何当代社会中,从种种敏感、危险的经验出发,很难不涉及到“政治”。我们未必要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那样坚持政治角度是“一切阅读与批评的绝对视阈”, 因为对泛政治化的警惕已经成为我们对意识形态社会的本能反应,但是应该承认他的阐释(“事实上,一切事物‘最终’都是政治性的”)有其合理性,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无法把政治经验在我们的现实经验中切割出去。
事实上,在艺术场域中发生的“政治”显然是更为广义的,不仅仅是事关公共事务的决策、管治,而且更包括了文化、身份、伦理等领域中的冲突与协调,这是在许多当代艺术家眼中的“艺术即政治”(art as politics)的真实含义。实际上,即使从“艺术非政治”(art- as-nonpolitical)的立场上看,《谈话》所表达的内心经验也是具有同样的艺术价值的,它无非是把一种真实经验成功地转换为视觉感受。在经历过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洗礼之后,艺术经验与政治经验之间作为二元对立的边界早已模糊不清。
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辉格解释》批判了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的立场上的历史论述,在我看来,巴特菲尔德的批判性观念中所包含的历史复杂性与辉格式书写的简单化问题与当代艺术中的历史记忆主题的创作也有内在的联系。在当代艺术的历史叙事中既有简单化的标签式作品,也有似乎是凭着直觉而力图还原历史情境的可贵尝试。巴特菲尔德强调的是对具体历史细节、偶然性和情境网络的重视:“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具体,他只在一个由事实、人物和种种偶然组成的世界中才会如鱼得水。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由时间和情境的作用而织成的网络。组成他故事素材的,正是种种偶然、种种联系以及各种事件奇妙的并存。他所有的技艺都要用于重新捕捉一个瞬间,抓住个别和特殊,确定一个偶然变故。……历史学家在本质上是观察者,他在观察活动的场景。”[9]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璜生作品中的那些在铁丝网上飘荡的纱布、摇晃的铃铛以及在墙上变幻的来自铁丝网的光影,无不来源于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像历史学家那样的观察者和捕捉者,那些铁丝网、纱布、沙发无一不是来自历史的细节和情境网络,无一不在宣示着一种以生命意志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隐喻着对固化的残暴与恐惧的挑战。
美国艺术家汉斯·哈克曾经在讨论他于1988 年在奥地利格拉兹市的市中心创作的《而你们曾是胜利者》装置作品的时候,强调有胆识的艺术组织者与艺术家的坚定合作能够使艺术产生巨大的政治作用。这次展览的组织者维尔纳·芬茨关于这次展览宗旨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认为这次展览“应该促使艺术家去探讨历史、政治与社会,从而索取精神空间,今天精神空间已处于预谋的、轻率的、逐步的衰退之中,它以被日常生活的冷漠所左右”。[10] 汉斯·哈克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其实艺术机构是具有政治性的地方。也可以说这是战场,社会上各种思潮在这里相遇。与人们想象的相反,艺术世界并不是孤立的世界。那里发生的事表达了整个社会,并且引起反响。”[11] 在今天,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它必须在表达个人的同时也表达社会,除了激起自己内心的反响之外还应该激起社会的反响。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放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中可以获得更多角度的阐释。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敏锐指出所谓当代与现代的界线远非那么清晰、确定一样,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也存在同样问题。罗伯特·威廉斯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现代主义逐渐显露出它不太像是一种彻底的断裂,而更像是现代主义的某种延续和强化—一种高级或超级现代主义,它的最重要的成就仍然可以被归属为一种批判事业的观念,即使它同样对批评性分析的可能性提出质疑。”[12] 他想说明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核心的“批判事业”即便是在被称作后现代的文化景观中仍未过时,他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艺术观的概括至今也仍有启发性。当然,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罗兰·巴特、德里达等等后现代思想家在思想与学术层面掀起的颠覆性巨浪与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更为内在的密切联系。约瑟夫·纳托利在《后现代性导论》中指出:“是的,的确存在着一场后现代的政治斗争”;[13] 在这场斗争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要做的最诚实的事情是释放思想,一种有效的政治需要建立在主观自由和文化自由客观性操作的基本原则之上。”[14] 这或许可以把后现代与现代主义在政治性场域中连结起来。
五、余论:对话结构与“剧场性”及“在场性”
前面在谈到《谈话》这组作品的时候说过,“对话结构”是整个展览的表述语言的语法特征,现在可以回过头再进行一些阐述。首先要把一些比较容易看作是“对话”的因素予以限定甚至是排除,比如在传统与当代之间,虽然从线条、墨迹、拓印等艺术语言中的确存在古典传统的因素,但是我宁愿把这些看作是以转换为自觉创作意识的出发点,而不是作为创作结果的展览的对话结构中的一方。作者在多组作品中反复寻求和运用的是一种对话式的语法结构,是同时在场、相互对峙、共同完成语义表达的结构性关系。例如,在媒材和作品形态的层面上,《缠》是铁丝与纱布在鼓风机催化下的对话,《界》更加是铁丝网架与铃铛、声音与光影的对话,《谈话》则是沙发与铁丝网的对话,但在这些可视、可感的对话结构之下,还存在着一层作者真正希望揭示的对话结构:安全与危险、遗忘与记忆、伤痛与治疗、文化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等对话性的议题。
这里的对话结构有点类似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论述的、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创造的“复调”结构,但是视觉艺术与文学的重大差异使回响在《边界/空间》中的声音、意识和观念无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那样各有其哲学的、宗教的或生活的观念,无法像小说那样表现出多种各自独立的、不受作者意识控制的多声部结构,并借以表现出作者自己也无法预设和统一的精神意识—在巴赫金的论述中的“复调”是破除了文学创作的“独白型”与哲学观念的一元论之后的最高级的对话形式。在王璜生《边界/ 空间》中的对话则是在作者的创作主题意识观念主导下的一种结构性安排,是在对于多种媒材与表现手段的综合性运用中的语法结构。
无论是符号的运用还是对话结构,都囊括在一个更大的场域中,这就是展览的整体性氛围。《边界/ 空间》的整体性氛围无疑是由其中的核心作品烘托起来的,这种氛围具有某种鲜明的特征,我想可以借用迈克尔·弗雷德关于“剧场性”和“在场性”的概念予以分析。弗雷德在他的《艺术与物性》(1967)中以“物性”切入,通过讨论“物”与环境空间的关系和对“剧场性”的批评而提出了“在场性”的概念。在弗雷德看来,“剧场性”就是过多考虑作品与观众的关系,因此极简主义(他更喜欢的概念是“实在主义”[literalist])追求剧场式的展示方式,关注观看者遭遇作品的实际环境,其布展方式总想要达到“场面调度”的独特效果。但弗雷德认为这从根本上与现代主义相背离,现代主义艺术总是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来构建一个经过转化的世界,作品应该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在任何一个时刻,作品本身都是充分地显示自身的”;观众对于艺术作品的体验不应该是直接融入式的参与,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作品进行反思性的静观,这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在场性”(presentness)。但是,他所批判的“剧场性”后来仍然在当代艺术中大行其道。[15] 实际上,我认为“剧场性”与“在场性”未必如弗雷德所坚称的那样僵硬对立、不可调和,一方面过分渲染环境的剧场效果固然会喧宾夺主、使作品本身被漠视,而另一方面观众没有场景氛围的吸引也难以投入到“反思性的静观”的境界之中。
在王璜生的这个展览中,《界》《谈话》《缠》《隔空》等作品无论从布置方式或审美效果来看无疑是具有某种“剧场性”氛围的,但恰好是这种氛围调动了观众在观看的瞬间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弗雷德所祈求的“在场性”并没有因此而无法产生。王璜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关于展览的“在场性“的很好阐释:“我想给观众传达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体验,每个展览首要考虑的就是观众自身的体验性,心身的体验。第二个是触动,观众能在面对作品时形成感知,有一种精神上的呼应。第三个是思考,我希望展览有回味的余地,能够引起公众更多的思考与追问。这也是此次展览所要传达的。”从中能感觉到一种尖锐的“在场”的品质和仍在进行中的时态—那种追忆历史、思考现实和挑战未来的品质与时态。
2017 年11 月23 日于广州从化流溪河畔
注释:
[1] 见CAFAM 为此次展览所作的专访:《游走于边界/ 空间:王璜生艺术中的冲突与诗意》
[2] 巫鸿:《王璜生:边界/ 空间》,2017 年7 月
[3] 由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自述,下引自述出处相同者不另注。
[4] 王璜生在本次展览研讨会的发言
[5] 同 [2]
[6] 参见简·罗伯森、克雷格·迈克丹尼尔《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 年以后的视觉艺术》,258-259 页,匡桡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 年
[7] 同 [1]
[8] 参见王璜生主编《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前言,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
[9] 巴特菲尔德的《历史的辉格解释》,第40 页,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 年
[10] 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75 页,桂裕芳译,三联书店,1996 年
[11] 同上,97-98 页
[12] 罗伯特·威廉斯《艺术理论:历史引论》,广东美术馆主办《美术馆》2006 年A 辑(总第十期),44 页,常宁生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
[13] 这是该书第六章的标题,潘非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4] 同上,133 页
[15] 此处关于弗雷德《艺术与物性》及“在场性”概念和相关论述,参见沈语冰为弗雷德《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写的论文式的“译后记”第三部分,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年
开放信息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逢周一闭馆)
每日16:30停止入场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烟雨路38号
咨询电话:020-87351468
预约观展:
通过微信公众号实名注册预约,到馆出示预约二维码、预约人身份证进馆。如需预约改期请先取消预约重新预约。每个成人限带1名儿童(未满14周岁)。
目前仅接受散客(个人)参观。
热门文章
-
广州影像三年展2025即将启幕,本次展览以“感知生态学”为主题,探索数字时代...
图片新闻